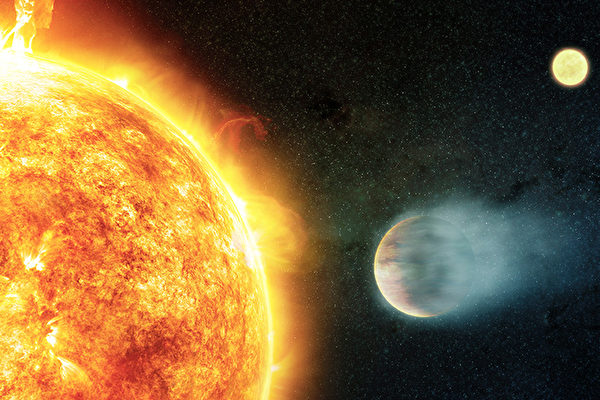初秋,午後的陽光從會議室的玻璃牆斜照進來。胡立民博士坐在窗邊,語氣溫和平靜,卻句句有力。「華人創業者最大的問題,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太聰明。」他頓了一下,微微笑著補了一句:「太聰明,反而容易孤獨。」
這句話讓我記了下來。 矽谷滿是聰明人,但真正能讓世界記住的,往往不是最聰明的那一群,而是能把聰明變成制度、品牌與信任的人。這,也正是許多華人創業者面臨的結構性挑戰。
一、為什麼偉大企業極少由華人創立?
華人創業者遍佈全球,勤奮、專業、智商高,但能成為「定義產業標準」的企業家,寥寥無幾。 這不是天分問題,而是環境與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胡博士說:「在美國,失敗不是污點,而是一筆學費。你可以跌倒、再起,法律和市場都容得下你。」
美國的創業制度是一張安全網——從創投體系到破產保護(Chapter 11、Chapter 7),從個人信用七年重建到知識產權法,整個社會鼓勵人「嘗試、錯誤、再出發」。而在中國或多數華人社會裡,失敗常是終點。沒有個人破產制度,企業倒了、創辦人傾家蕩產、信用報銷, 許多人因此選擇保守經營,不敢冒險創新。制度的不容錯,使創業者成了走鋼索的人。這樣的環境下,創業變成套利,而非創新。「在矽谷,創業是為了改變世界;在很多地方,創業只是為了求生。」胡博士輕聲說。
二、台積電為什麼能成功?
說到華人世界的成功典範,胡博士第一個提到的是台積電。「它的成功不靠運氣,而是靠制度。」張忠謀創造的,是一個獨特的治理模式。他不與客戶競爭、專注代工,用「中立」換取全球信任。台積電的力量,不在華麗宣傳,而在紀律與準時。每一次良率提升、每一個交期準點,都是信任資本的累積。「那是極少數把信任當產品的公司。」胡博士說。 他停了一下,像在思索:「台積電證明了,制度化的信任也可以是競爭力。」
三、黃仁勳為什麼能成功?
相比台積電的理性,黃仁勳的 NVIDIA 是一場激情。 他用二十年時間,把一塊繪圖晶片變成全球 AI 運算的心臟。他講故事的能力,近乎天才。「他不說 GPU,而說『加速運算時代』;不談晶片,而談人類未來。」胡博士笑著說,「那不只是技術,更是敘事的力量。」NVIDIA 的成功,不只是賭對 AI,而是早在十多年前就打造了 CUDA 生態。 當幾百萬開發者把「學 GPU=學 CUDA」當成常識, NVIDIA 已不只是公司,而是基礎設施。「他懂得授權,也懂得信任。公司成長靠制度,不靠個人。」胡博士說,這正是多數華人創業者最難跨越的一步——從創辦人中心走向制度中心。
四、為什麼中國創業者更難?
「不是人才不夠,而是風險太高。」胡博士語氣平靜。中國的創業環境「快」但不「穩」。 政策與監管變化頻繁,融資週期短、資金焦慮高,外資限制與出口管制也讓跨境科技公司如履薄冰。「在這種環境下,沒有人敢押十年,只敢賭兩年。」
胡博士說。他頓了頓,補了一句:「但偉大的公司,從來都要十年以上的積累。」
矽谷之所以能吸引全球創業者,
靠的是制度與文化的雙重容錯:
— 法律允許重來,
— 市場鼓勵冒險,
— 投資人接受失敗
— 社會尊重試錯。
「這裡的創業者能失敗十次,還有人願意投第十一回。」他笑著說。
五、今後可能的成功方向
面對全球競爭,華人創業者要走出舊思維。胡博士歸納出四個方向:
一、組多族裔團隊。
華人擅長技術,但需要與印度人、美國人、歐洲人合作,讓產品從 Day 1 就具全球語言。
二、選結構性缺口。
半導體設備、AI 應用、氣候科技、醫療自動化、跨境合規工具—— 這些都是「東方勤奮+西方制度」可以結合的市場。
三、制度先於產品。
創業要想進入全球鏈條,先要做到「合規、透明、可信」。懂 GDPR、出口法規、稅務與審計的團隊,
才有機會贏得國際客戶的信任。
四、長週期思維。
不要追風口,要築橋梁。 真正留下來的企業,都以十年為單位思考。
六、從孤島到群島
訪談結束時,陽光慢慢從窗外退去。
胡博士的語氣依舊溫和:「聰明不是問題,孤單才是。」他說,華人創業者往往在技術上是強者,在制度上是新手。 我們太追求完美,太怕丟臉。但偉大的企業從來不是天才的勝利,而是制度、文化與人性的共生。矽谷靠信任,台積電靠紀律,NVIDIA靠敘事。 華人要成功,就得學會把聰明變成協作,把勤奮變成長期主義。他笑著補了一句:「成功不是你爬得多高,而是跌倒後能不能再站起來。矽谷,就是這種不怕摔倒的地方。」 當我們願意與世界同行,華人的創業故事,才會真正開始。
胡立民博士聯繫電話
(510)909-8832
郵箱liminh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