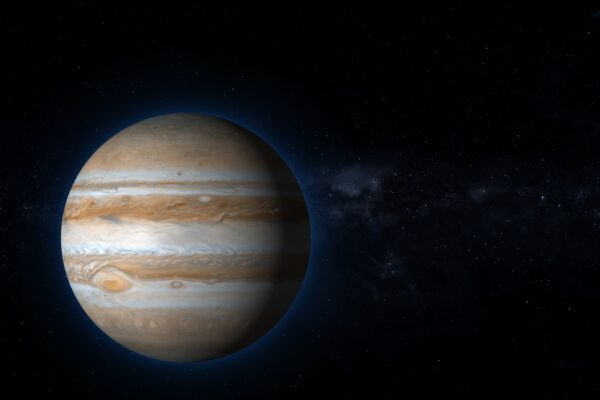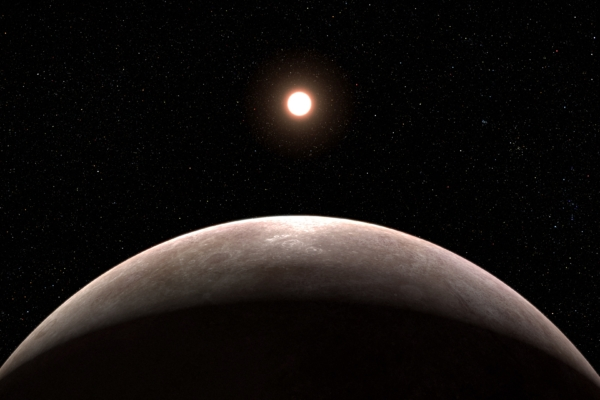【2024年04月13日訊】中共1949年5月占據上海,初期中共對於上海的接手還比較順利,當時,政權的改換「並沒有引起民眾大的風波和反抗」。然而,1950年後上海農村卻發生了農民抗議活動,那這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麼呢?《中國當代史研究(三)》一書中的文章《建國初期新政權在上海郊區農村的征糧問題(1949-1953年)》深入探討了這個問題。
「三征」相連又遭災,農村各階層均無力應對
由於南下的大部隊需要大量的糧草,因此中共占領上海後,當務之急就是籌糧。很多南下的部隊路經上海,外加物資調運、各種交接,人員往來頻繁。據中共華東局計算,從1949年4月中到9月中共5個月內,僅野戰軍所需糧食就達九億斤。
中共一向是通過向農民徵收公糧來解決軍隊的糧草問題的。因此,1949年3月,中共就啟動了一輪向農民征借糧食的工作,後續又進行了夏征和秋征,一年之內三次征糧,令上海農民苦不堪言。
第一次由於征借量不大,每畝10斤至20斤,所以不管是地主還是農民上交的都很痛快。
5月底,大批工作隊下鄉準備開展夏征工作。政策是「以戶為單位,以1948年冊載賦額為標準,每元賦額徵收稻麥80斤,草40斤;夏季征小麥,秋季征稻穀;不產稻麥之土地,得按市價折收其他農作物或代金,出租田應繳之公糧公草,夏季由業主負擔、佃戶代繳。」
對此,農民紛紛抱怨:「以前我們只要交租不交糧,交租也只是秋季交,現在不僅交租交糧,還夏秋兩季都要交」;「生活比過去低了,過去吃三頓米飯,現在吃二頓小麥還吃不上,靠現在的政府什麼也沒有」。
而且當年又發生了颱風襲擊和特大洪澇災情,棉花和大豆損失慘重,稻田收成減半或僅至常年產量的七成。但中共卻對災情不關心,仍然決定「夏征不應因水災而延緩和放鬆」,僅對全部土地被淹地區實行「延長半月」的緩徵期。
緊接著秋征又在9月份開始了動員工作,中共號召通過減租、訴苦、算帳、反黑地等鬥爭方式,來促進繳糧工作。因此查黑田、劃成分成為秋征的最大特色。
中共提出「一人瞞田,大家吃虧」、「地富瞞田,農民吃虧」的口號,挑動農民與地富的對立,為了刺激農民檢舉揭發地富黑田的熱情,還承諾農民可以從對地富的罰款中得到一定比例的獎金。群眾大會上,骨幹分子用控訴來挑起群眾的仇恨,使鬥爭逐漸升級。
農民被發動起來後,各鄉又開始劃分階級成分。在農民心中,中國鄉村固有的宗族、地緣關係是至高無上的,中共通過劃分階級打破了鄉村這種傳統的關係,代之以階級和對立。鄉村中具有話語權的地主、鄉紳紛紛被打倒,在公糧繳納額度上又實行貧雇農負擔輕,地主富農負擔重的政策,通過收買和利誘貧雇農,使他們意識到,階級成分與個人的公糧負擔數、政治地位乃至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農民們逐漸被顛覆了傳統的思維而接受了中共的意識形態。
在上海郊區農村,地主並非單一依賴農業收入,農民也經常拖租、抗租,實際交租額並不高,地主也不去深究。所以,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關係並不緊張
如柳亞子家有田甚多,他1927年離家後,家中的田產地契都由管家張榮生代為管理,收取租米則是帳房沈某負責。早在1947年,柳亞子便通知張榮生不要再收租米,並登報與沈某解除了僱傭關係。
沒有剝削、壓迫概念的上海農民對階級劃分更沒有概念,有的認為誰家窮誰就是貧農,誰家有米吃誰就是富農。以至有人說:「解放軍喜歡勿勞動的人,勞動終是勿靈格」。
階級成分直接影響到公糧負擔的多少。中共新政策將公糧分為基本公糧和累進公糧兩種,對貧農只徵收基本公糧,地主富農則在基本公糧之外還要徵收累進公糧。中農則負擔一小部分累進公糧。
中共宣稱「公糧的負擔率貧農一般為5%~8%;中農10%~15%;富農20%~40%;地主35%~50%」。然而,當時上海農民的負擔率已經遠遠超出這個標準,如上海縣三林區荻山鄉10戶典型戶,1949年夏秋兩季公糧負擔率,貧農為15%~66%;中農60%~88.9%;富農竟達209%。
「三征」相連,受災減產,外加公糧負擔率奇高,導致很多地主只能變賣家產或工商業來繳公糧;稍有積蓄的富裕戶叫苦連天;一般的中農、貧農也苦不堪言,農村中各階層均強烈不滿,對繳納公糧愈加牴觸。
1950年1月,1949秋征繳納公糧最多的鄉才完成七、八成,有的僅達四成,還有的地方一點都沒有交。
中共的暴力強征致群眾反抗頻起
中共蘇南區委1950年3月編寫的《川沙縣調查資料》顯示,未到年關,農民手中的糧食已經所剩無幾,不少地方出現了無米無糧的狀況。
如:有的鄉20%的農戶生活已經很困難;有的鄉無米下鍋者已占10%;有的鄉30%的農戶沒有吃的;一區顧東鄉,已經有50%的人沒有飯吃;最嚴重的四區新民鄉已經有80%的人家沒有吃的了,只好吃野草、吃糠等。
下到基層的一些幹部也表示,「公糧、稅收任務太重」,並對中央、華東局以及各區、縣委的決議存有異議。但區、縣一級幹部卻認為,征糧任務完不成,主要是基層的鬥爭性太差了。「鬥爭地主還不夠狠,很多地富想拖交抵賴;群眾覺悟性不高」。
基於這種判斷,中共幹部強征、硬征、催糧逼糧的狀況頻出,川沙縣「欽公鄉24戶地主在鬥爭中被迫答應交糧高達544000斤,但實際上只能交出7900斤」,差距竟達68倍!還有的區縣幹部開會時強迫基層幹部完成硬性數字規定,不同意不能回家。
1950年4月的《中央公安部關於新區匪特暴亂奪糧情況的綜合報告》中稱,上海郊區接連爆發以「抗糧,反征糧,打倒北方政府」為口號的農民「暴動」和「騷亂」,且「帶有相當規模的群眾性」。而與此同時,華東、華南、華中、西南等其他共產黨新占領區也都先後發生了大範圍的「暴亂」,多數都與公糧負擔過重、征糧方式過激有關。
如,1950年11月底,馬橋區的農民去縣委請願,「要求減免、減輕公糧負擔」。這本是一樁因中共強征公糧引發的群眾自發抗議活動。但地委負責人卻不認為中共自身的政策有問題,而是馬上聯想到階級鬥爭,將這次請願事件認定為是有敵特叛徒6人策劃組織的一起反革命抗糧事件。
正因為公糧的負擔不合理,各階級的負擔比例都在加重,公糧徵收的對象擴大化,地富中農、貧雇農都起來抗糧。金山、奉賢、松江縣等地紛紛爆發各種武裝抗糧的運動,有40多名中共地方幹部被殺。
但在中共的宣傳中,卻強調是地主在對抗征糧,只要把地主鬥垮斗蔫,就能完成征糧任務。導致各地對地主的鬥爭升級,出現了打、罵、拴、罰跪、剝衣,以至打死的現象。如閔行區委書記因下屬打死2人而向上級請求處分,縣委卻答覆「打得好」,因而區委書記認為打死人無所謂。
1950年夏土改試點啟動後,亂打亂殺的混亂現象更加嚴重,「蘇南各縣已經關了1700餘人」,各縣處死人數都有幾十人之多,如川沙處死22人,青浦處死43人,松江縣處死36人,南匯區處死31人。同時還有多人不堪壓力自殺。
對地主的用刑方法包括:吊打、叩頭、剝衣、跪磚、站冰、遊行、讓孕婦罰跪、拖老人遊街等等,82歲的地主王彩珊,被剝衣吊打,打得眼珠突出,雙目失明;還有讓地主在公審會上跪在碎磚上,昏死過去後又被噴冷水,將其激醒後再接著斗。
很多原本已經居住在上海市內或逃亡至城市的地主也被勒令回鄉,大多數都遭到「體罰肉刑、剝衣冷露,戴高帽遊行、不給飲食」等嚴厲懲治。
1951年底,上海農村土改基本完成,但中共通過土改來促進征糧的願望卻落空了,因為多數農民土改後,生活「與解放以前差不多沒有顯著改善」。而且,土改後雖然田地歸了農民,但公糧攤派卻進一步增加,農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並未緩解,反而加劇了衝突。
據《松江縣塘橋鄉征糧騷動事件調查報告》記錄,1951年12月6日,千餘名村民聚集,將聞訊趕來的區委幹部鄭志九按在地上毆打,前後被打了三次,鄉農會主任顧仲齋亦被打傷。12月7日晚,九個村千餘人召開大會,喊出的口號是:「要減免、要6畝折1畝,哪村先繳糧全到那村吃,區裡捉一個,我們去十個,捉十個,我們全去」。12月8日,縣委武裝部率領公安部隊對村民進行了武裝鎮壓。
村民們要求的6畝折1畝,是國民政府時期對於盪田(半高地)實施納糧的標準,有的盪田甚至達到9畝折1畝,而且征糧額度從未超過收成的35%。而中共卻在1950年將盪田改為3畝折1畝,1951年又改成1畝抵1畝,導致農民強烈的不滿和牴觸。農民們感覺:「共產黨是一步緊一步,總歸叫你吃不飽,餓不死,結果是國富民窮」。
1952年,又發生了多起農民自殺、村民打架、剿糧船沉船等事件,農民們經歷了之前中共的暴力和鎮壓,所以被逼糧無奈後選擇自殺的人數非常多。
黃炎培與柳亞子上書毛澤東,民主人士漸失話語權
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是上海川沙縣(今浦東)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柳亞子是吳江人,1950年初,黃炎培就不斷收到親友來信,反映農村征糧中的問題。1950年4月,黃兩次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反映有關征糧的問題,以及他了解的川沙、南匯、奉賢三地的情況。他還有意幫中共挽回人心:「必須快快予以有效的處理,必須先把人心挽回過來」。
毛致電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要求他轉告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將情況報告上來。陳丕顯於5月28日向毛澤東報告,稱征糧中出現了一些問題都已經得到解決,這些問題都是因為地主對繳納公糧的對抗和拖延造成的,至於個別打人、抓人事件,都是因為地主惡霸抗交公糧,激起了民憤。陳丕顯還認為黃的信中所述「有些與事實未盡符合」。
本來只是希望通過毛澤東的關注而使事情得到糾正,然而,1950年底,黃再度收到家鄉八封來信,信中舉出的極端事例更多了。黃將整理好的十二封信和一張統計表交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金誠,並建議:「最好派個人到下邊去看看」。
與此同時,柳亞子也在1950年12月寫信給毛澤東,反映自己家鄉吳江縣「頗多『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的問題。柳家雖已兩年不收租,仍被逼交公糧,只得由其女寄去600美鈔抵交公糧。而柳家在鄉家人沒有飯吃,生活困難,柳亞子1950年10月寫信給相關人員,要求歸還1949年被征借的糧食,信中稱當地幹部做法實「與綁匪對付肉票無殊」。
兩位民主人士先後向毛澤東反映情況,似乎引起了毛的重視,在毛安排之下,黃炎培得以前往上海及蘇南考察。然而,身為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在考察過程中卻被華東局密切監視。華東局各級幹部表面上對其很尊重,但心裡對其卻極不以為然。饒漱石與黃的談話並不客氣,陳丕顯也給幹部們打氣,讓大家不要畏縮。
得到了上級的支持,地方幹部們也準備好一套說辭對付黃炎培。對黃提到的高形鄉黃三三之妻被逼交公糧而吊死一事,地方幹部稱,經調查「本人神經病發作,早在秋征之前即己上吊死亡」。對多次被吊的沈李氏,地方幹部聲稱,「本人確為大地主,家有房產2260餘間,為當地惡霸」。因其「不聽勸告,頑固對抗的囂張氣焰,激起了群眾公憤,是群眾將她吊了起來」。
黃並不相信地方的說辭,認為「說真話者不易找」。他認為「農村中的最大問題,是還有恐怖情緒存在」。回北京後,黃只是口頭表示上海之行大體滿意,但並沒有對上海農村的土改或征糧有任何積極的或讚揚的話語。
對於黃炎培和柳亞子反映的問題,中共無論是高層還是地方,所持態度一開始就是一致的,他們只是表面上說要調查處理,但實際上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做錯的地方。因此,黃炎培的南行無功而返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毛澤東的真實態度也是一樣,返回北京後,黃2月17日就接到毛送閱的廣東、廣西對鎮反工作糾正寬大無邊錯誤的兩份材料。毛在信中說:「……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必須採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言外之意,為了政權鞏固,鎮壓必須堅決,而這就是中共的態度,也是毛澤東的態度。所謂「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面對毛如此的表示,黃還能有什麼作為呢?事實上,中共建政後,早已經將自己口口聲聲大談特談的民主制度棄之腦後了。
結語
中共占領南方地區後,首要的任務就是征糧,當時中共要求新占領區先不進行土改,為的是保證征糧任務的完成。而1950年進行的土改,其目的仍然是要讓農民與地主對立起來,以更好地完成征糧任務。
強硬征糧和土改鬥爭,也是中共在新占領區建立暴力政權威懾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不但完全摧毀了中國鄉村宗族自治的傳統,代之以階級對立的農民翻身運動,而且,其對農民的盤剝也日漸趨緊。
中共政權所到之處,所有的矛盾都被划進階級鬥爭的框框中加以解決,以至於各地農民的反抗都遭到了中共的武裝鎮壓。之後,交不起公糧的農民只有選擇自殺一條路了。
可見,中共在農村的階級鬥爭、鎮壓地主並非為了所謂的反壓迫,為了農民有飯吃等等,而是為了用暴力手段對農村各階層強制灌輸中共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