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路小玉採訪報導】他曾是一個被世界遺忘的孩子,在污濁與飢餓中成長,在嘲笑與排擠中求生。他曾在冰冷的樓頂尋找解脫生命的方式,也曾在垃圾桶邊見證無言的父愛。
Cyrus,這位來自中國的年輕法輪功學員,站在自由的土地上,向人們講述著那段他們一家在黑暗中掙扎求生的歲月。
「那段時間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活著」
「同學不理解為什麼我的手、衣服總是帶著油污;我的臉每到冬天就會凍傷,青紫的臉帶著結痂,手皸裂的像是外祖母的手,家長會我們家從沒人去過⋯⋯我在學校擔心被排擠、嘲笑,回家則是不停勞作,拚命幹活也會被罵……那時的我,眼前只有望不到盡頭的黑暗。」Cyrus對記者說道。
年幼的他,曾經反覆思考終結生命的方式。最終他選擇的,是二姨家樓頂的一個角落,下面是一艘廢棄鐵船,再下一層是水泥地,當時還在上小學六年級的Cyrus想:「從這裡跳下去肯定會死。」
正當他要邁出那一步,想想自己還有沒有什麼遗憾,腦中突然閃現出一件事——那次與警察的對話,他曾告訴他們「天安門自焚」是造假。「如果我真的跳下去,中共絕不會承認我是因為他們的迫害,才落到這一步,他们一定會拿我做文章,繼續欺騙世人。我的父母怎麼辦?我的姐姐怎麼辦?」
Cyrus說:「经过痛苦的挣扎,我最终决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不让邪恶的迫害得逞,也不让我的家人因我更加痛苦。」
如今,脫離了中国大陸的痛苦歷程、重拾信仰的Cyrus,在美國的自由天空下,重溫著1999年中共對法輪功迫害開始前,全家修煉所帶來的身心巨變,不禁百感交集。
他原本也有一個溫馨幸福的家庭,而這一切要從Cyrus的父母修煉法輪功說起。
脾氣火爆的父親變了一個人
Cyrus曾听父母说,年幼时父親脾氣暴躁,幾乎沒有幾天太平日子;母親體弱多病,渾身沒有幾處不痛的地方。
直到1998年父親接觸法輪功,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那时Cyrus的父親一直有練氣功的習慣。1998年正月,父親從鄰鎮聽聞法輪功和一般的氣功不一樣,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對心性要求特別高,於是興匆匆地跑去鄰鎮學法輪功。
「自那以後,父親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不再亂發脾氣,甚至和人發生矛盾時,會想想是不是自己的錯,說話做事都要求自己盡量符合『真、善、忍』,對比之前動不動就惡語相向甚至出手打人,簡直像變了個人!」
看到父親如此大的轉變,Cyrus的母親也試著一起修煉,不久她身體上的病痛逐漸消失,修煉之前難以走直,後來這些症狀都沒有了。「這讓我媽媽更加堅定地要修煉下去。」Cyrus说。
「爸媽觉得他们身心发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應該把這麼好的功法介紹給別人,便開始在村裡,甚至到鄰村洪傳大法。那時他們帶著錄音機、橫幅,租房播放師父的九講班錄像,義務教功等等。」
「那段時間也出現很多神奇的事情,」Cyrus說,「比如,村里有一位老奶奶臥床很久,身體越來越差,家人感覺她活不久,便準備好了棺材、壽衣。碰巧我父母去洪法,結果老奶奶修煉了之後身體越來越好,不久能下床了,能正常煉功了,半年後看起來和正常人差不多了。這種神奇故事比比皆是,鄰居街坊之間也口耳相傳。」
那段日子,村裡煉功的人越來越多,他父親也成為當地輔導員。

進京上訪:守護良知 為信仰發聲
由於修煉法輪功人數越來越多,引發了中共時任黨魁江澤民的妒忌。1999年7月20日,中共全面發動對法輪功的鎮壓。
幾個月後,鎮派出所的警察突然闖入Cyrus家,搶走了橫幅、書籍、磁帶、播放設備等私人物品,並將父親帶走,半個月後,父親才從拘留所被釋放。
「那一年,我還只是個蹣跚學步的孩子,姐姐不過9歲。」Cyrus說,「那時我還小,記憶不太清楚了,但聽父母說起過那時的故事。」
由於全家從大法中受益,他的父母覺得要向政府反映情況,告訴他們真相,於是和本地的同修準備一起去北京天安門,為大法說句公道話。父母也不知道此行有何遭遇,但出於良心決定要去。
2000年3月初,父母帶著他和姐姐,一家四口來到天安門廣場。
長大後,Cyrus曾聽媽媽講述那時的經歷:「媽媽一隻手抱著我,一隻手和爸爸一起拉著寫有『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可是大約一、二分鐘警察便趕了過來,不由分說地從我父母的手中扯下橫幅。爸爸趁機又從包裡拿出準備好的另一個橫幅正要拉開,警察立馬把我爸爸打倒在地,用腳踢、踩爸爸的臉。」
「警察把我們帶進一個高樓,然後大人就被戴上手銬,我和姐姐在旁邊哭了起來。」
當天還有其他地區的同修陸續來到天安門,被抓的人越來越多,認明了身份的學員,警察會通知他們當地的警察來接人,第二天Cyrus一家便被本地警察接回家。
這次上訪,父親被非法勞教三年,母親一年。兩個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父母的照顧。
姐姐的小三輪車 載著童年的風與淚
父母被非法關押後,Cyrus最初跟姐姐一起由奶奶照顧。但奶奶在Cyrus出生前經歷一場車禍後腦子有些不正常,「她做的飯菜經常不能吃,有時候不熟,有時候味道很奇怪。」「但是我印象中奶奶很疼愛我,有次半夜我喊餓,奶奶馬上起來給我煮麵吃,」Cyrus說,「雖然面很難吃,但我很感謝奶奶對我的照顧。」
但這樣的時光也沒能持續多長,薄薄的家底吃空後,姐姐就帶著Cyrus去親戚、鄰居家蹭飯吃,走的時候再討點。
「那時候,姐姐到哪裡都會騎著小三輪車帶著我,遇見一些大人謾罵、嘲笑,姐姐也當沒聽見繼續走。
「那時的我,大多時間是無憂無慮的。也許是因為當時年紀小,聽不懂那些謾罵和羞辱,也感受不到外界的惡意。
「後來隨著我逐漸懂事,我開始理解了自己的處境——在別人眼中,我是『邪教家庭』的孩子(注: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父母帶我和姐姐去天安門『自焚』,說我們一家人不正常等謠言四處流傳(而其實,『天安門自焚』是中共自導自演的騙局),越傳越離奇,跟我同齡的孩子也被家長教著不要和我接觸,有時村裡的孩子聚一起趕著罵我,我越來越感到悲傷和痛苦,再回頭想想姐姐的處境,那時她該有多難啊!」Cyrus說道。
姐姐11歲被拐、險喪命異鄉
母親被勞教滿一年後,被各種理由送進洗腦班、拘留所拒不釋放,2002年8月左右才被釋放,那之前家里早已長期無法生計。
2001年夏天,Cyrus的姐姐為了家裡吃喝有著落,被附近村子的一個人販子騙去乞討。
「眼睜睜的看著一直照顧我的姐姐離開,我心裏無比難過,每天都盼著爸爸媽媽和姐姐能夠回來。」Cyrus回憶道。
「人販子把我姐和十幾個年齡不一的孩子一起帶到另一個城市,孩子們分布在市場、學校、車站等人多的地方,團夥裡的大人躲在不遠處的人群中監視著孩子們的舉動。姐姐脖子上掛著牌子,在車站附近下跪乞討。姐姐雖然命途多舛,但也是有自尊心的人,這一點一直讓人販子感到不滿,抱怨她討錢太少,不肯拉下臉像別的孩子那樣努力賣可憐。
「一次姐姐被摩托車撞傷,渾身劇痛,牙齒被撞掉了,回去後想和領頭的要點錢去醫院,可他們卻說我姐姐總是討不來足夠的錢,這下被撞慘了,錢就好討了,於是強逼著姐姐忍痛繼續當街下跪乞討。
「後來姐姐討到的錢他們還是不滿意,就把姐姐賣給了車站附近賣土豆餅的小販夫婦,他們沒有孩子,買下了我姐姐,強逼她喊他們爸媽,姐姐最初不從,便被關在一間小房子裡削堆積成小山的土豆,偶爾給一點水和吃的。飢餓難耐之下姐姐最終選擇了妥協。
「逐漸地,小販夫妻放鬆了警惕,半個月後一次偶然的機會,小販夫婦忘記了鎖院門,姐姐一路狂奔找到了一個派出所,姐姐馬上說了自己的情況和老家地址,再一路兜兜轉轉,姐姐被警察送了回來。
「回想第一次聽姐姐講述這段遭遇時,我停頓了很久接不上話。這次為了接受採訪,我又和姐姐聊起往事,她緩緩地回憶著細節,我再次哽咽難言,內心的痛苦難以言表。我姐那時僅僅是個11歲的小女孩,卻險些在車禍中喪命,之後又被拐賣,如果她沒有逃出來,真不敢想像還會經歷什麼。於是我對姐姐說:『咱們還是別再回憶了,就到這兒吧。』」Cyrus娓娓道來。

垃圾桶裡翻出的奶油蛋糕
在2002年8月母親獲釋、2003年父親結束冤獄後,一家人終於短暫團聚。
當時年幼的Cyrus承受著社會被中共強加的謊言的壓力,令他內心總是處於緊張不安之中,遭到同齡孩子的孤立,讓他性格變得孤僻。
在中共當局持續的刁難騷擾下,父母被迫帶著Cyrus去外地謀生,姐姐在老家讀小學。
在新的環境,沒人知道Cyrus的過去,他逐漸敢開口和同學講話,性格也慢慢開朗起來,甚至交到了一些朋友。而姐姐在老家由於承受不住壓力,小學未讀完便輟學了。
Cyrus說,父母當時靠撿垃圾、收廢品維持生計,雖然家裡仍然貧困潦倒,但總算能喘口氣安身。
「有一次,爸爸從垃圾桶裡翻出一塊吃剩的蛋糕,托著它笑著招呼我來吃。我害怕地拒絕了。」Cyrus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的奶油蛋糕,但由於是從垃圾桶裡撿出來的,白色奶油像是壞掉的食物,我感覺很害怕、不敢吃。爸爸見我不吃,就自己笑著吃起來。那個畫面我一直記著。」
希望乍现时 兒時夢魘重現
後來Cyrus的父母改做水泥袋回收,由於不怕髒、不怕累地辛勞,家裡慢慢有了些積蓄,「我過生日和過年的時候也能買新衣服了,姐姐也來到這座城市找了個工作,與我們團聚。平時爸爸媽媽還能給我們買一些零食了,那段時光,我感覺好像一切都有希望了。」
可是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從未停止,在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惡行被曝光後,Cyrus一家人決定揭露中共的惡毒和謊言,加大力度把真相傳給被蒙蔽的世人。
他們常把真相資料投遞到信箱或居民院落,也在公園等公共場用噴漆寫下「法輪大法好」字樣,還手寫真相小紙條,放進好看的紅包放在公园里,還把真相寫在流通的紙幣上花出去。
2008年10月的一個週六,Cyrus的父母又像往常一樣出去發資料,後遲遲未歸。直到傍晚來了一輛警車在院門口停下,Cyrus猛然感覺不妙。警車門一開,父親帶著手銬、搶步子趕在警察前面走到院子门口,急迫小聲地對Cyrus說:「藏起來!」
Cyrus回憶道:「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趕緊衝回房間鎖上門。我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那麼多的大法書、師父法像、真相資料能藏到哪裡。慌亂中我不知道院門何時被打開,外面的警察大喊了聲『開門』,我下意識地用身體頂著門,想阻止他們進來,卻被緊隨而來的一腳踹門重重地撞摔在地,他們破門而入,搶走了家裡的書籍、光碟、真相資料等等。
「警察走後,我一個人完全懵了,哭了起來。又想起很小的時候父母被迫害,記不得具體什麼時候了,我在老家門口,想跳到警車引擎蓋上阻止他們帶走我的父母,卻怎麼也跳不上去,還被一把抓了回去,這次又是一樣的無助和絕望。
「恰好那幾天姐姐去了外地,手機也被搶走了,想聯繫姐姐也聯繫不了。一瞬間彷彿又回到姐姐被騙去外地乞討的那一天,一家人又只剩下我一個。我坐在被翻亂的撒著香灰的床上,盯著裝著爸媽頭天晚上給我買的兩雙新運動鞋的袋子久久不動,我也不記得那晚怎麼睡著的。」
隔天,警察再度上門將Cyrus帶走,假借「問話」之名,想套取父母的真相資料來源,Cyrus把真相資料上看到的內容講給他們聽,拒絕配合進一步審問,他最終被帶進警察局。
兩天後,媽媽設法打電話將Cyrus委託給二姨和表哥。這次,他母親被非法判刑七年,父親則被非法判刑七年半。

Cyrus再度被迫與父母分離,又回到了老家,由二姨收養。
寄住在二姨家時,警察每隔一、兩週就會騷擾他。一次警察逼迫他拍視頻,想以此來迫使被非法關押的父母放棄修煉。
Cyrus說,他當時強忍情緒,除了問候之外,便是機械地重複警察的話,盡力用笨拙的演技讓父母一眼看出他並非自願。
人生中最痛苦的時光
在Cyrus的記憶中,寄住在二姨家的那段歲月,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時光。
他二姨其實在1999年「7.20」迫害前,因耳聞法輪功祛病健身的奇效而走入修煉。然而,迫害開始後她因恐惧中共的邪惡手段便放棄了。
這個家庭其實早就看清中共的殘暴。家族長輩早在文革期間就已有多人死於中共之手。一位爺爺僅僅因為把毛澤東像掛在自行車籃子上,被指「對領袖不敬」而被批鬥致死。而Cyrus的外祖父因出身地主家庭,父親被槍決、家產被沒收,被劃為「黑五類」,整個童年都是在欺凌與謾罵中成長,長大後也只能與同為「黑五類」的外祖母成婚,才有了後來的家庭。
那段時間,Cyrus轉學到二姨家附近一所小學繼續讀書。剛開始,他極力隱瞞家庭背景,也結交到一位朋友,兩人放學一起回家、聊天。「我真的很開心。」然而突然某一天,那位朋友突然開始躲著他,甚至故意加快或放慢腳步甩開他。
「可我不願意放棄好不容易有的朋友,便逮著機會找他說話,有一次他開口告訴我,由於我父母修煉法輪功,他爸媽不允許他跟我再有接觸。」
這句話讓Cyrus心如刀割,也讓他開始意識到:自己不得不學會接受這樣的現實。在這之後,他失去了不少朋友,他同時也學會了接受。令Cyrus感動的是,有幾位朋友明知父母不許,卻依然偷偷和他一起玩。
二姨家是開修車鋪的,不上學的時間,他就幫忙幹活。
「很多大人都驚訝我小小年紀就會修拖拉機。我一手繭子,胳膊上還有肌肉,能拆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大輪胎,一身糊的是洗不淨的油污,衣服沒有一件乾淨的,逢著農忙時期更是修車、田裡農活兩不誤。我的好朋友知道我每天那麼勞累,會為我感到心疼。」
「肉體的累反而能讓我精神麻木,不去想太多。」他說,「可每當夜深人靜,忍不住的悲傷會撲面而來,才是最難過的!我思念父母和姐姐,那種無助、對未來的恐懼和人生的絕望,總是讓我久久難以入眠。」
上了小學六年級,隨著年齡漸長,他的絕望越來越深。
「同學不理解為什麼我的手、衣服總是帶著油污;我的臉每到冬天就會凍傷,青紫的臉帶著結痂,手皸裂的像是外祖母的手,家長會我們家從沒人去過……我在學校擔心被排擠、嘲笑,回家則是不停勞作,拚命幹活也會被罵,二姨和姨父吵架之後不痛快也會拿我出氣⋯⋯那時的我,一直想不明白,我為什麼要活在這個世界上,眼前只有望不到盡頭的黑暗。」
他開始思考結束生命的方式。最終,他選擇了二姨家三樓的樓頂。樓下是廢棄的鐵船,再下面是水泥地。「我確信從這裡跳下去會死。於是那一天起,我每天都會偷偷爬上樓頂,用石頭寫下倒計時。我恐懼死亡,也知道人不可以自殺,但是面對3個月的倒計時時,看到數字一天天的減少,卻少有的開心。」
在最後一週,二姨發現了他的異樣,雖並不確知他的計畫,但已不准他再上樓。
隨後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2013年夏天,Cyrus的媽媽提前出獄。短暫團聚後,她便前往姐姐那裡打工,賺錢養家。半年後,父親也出獄,與母親一同去外地謀生。
2014年7月,Cyrus考上縣城高中,開始了嶄新的求學生活。
重拾信仰 決心此生一修到底
雖然高中三年Cyrus仍與父母分隔兩地,但每年寒暑假可以短暫相聚,他重新過上了正常的學生生活。不過,經歷過童年的種種,Cyrus對修煉產生了猶疑,也擔憂父母再度遭受迫害,因此鮮少再打開法輪大法的主要著作《轉法輪》。
直到高三結束後的暑假,沒有了學業的壓力,在父母的引導下,Cyrus重新拾起法輪功書籍閱讀。他說:「師父的法理讓我心境漸漸明朗,我不知不覺中放下了對過往欺凌過我的人的仇恨,隨著心中的陰霾逐漸散去,多年來困擾我的失眠症狀也慢慢消失了,我變得更加開朗自信。每天都很精神,做事會更為別人著想,每天都很開心,對我來說彷彿新生!」
開學前,Cyrus陷入內心的掙扎——大學生活該怎麼面對?要不要繼續修煉?
那一段時間他思考了很久,由於學法他已經知道了人生的意義,說放棄真的不願意,可是離開父母獨立修煉還是讓他心有餘悸,一時間怕被舉報,怕被帶上警車,怕被判刑等等思想甩也甩不掉。他說:「此時,我想起了師父在《精進要旨》〈溶於法中〉開示『朝聞道,夕可死。』的道理,瞬間如釋重負,我放下了心,決心此生一定修煉下去!」
大學期間,Cyrus每天堅持學《轉法輪》。一次偶然的機會,有同學教他翻牆,他便開始閱讀師父的更多著作。那段時間雖然不像一般人的大一生活那般熱鬧,他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內在充實、平和、沉穩。「第一學期結束前,我和高中朋友聊天,他們都說我好像變了一個人,我笑著問他們我怎麼變了,他們說我變得不爆粗口,性格穩定,更善良了。」
「在宿舍裡,我主動做家務、配合同學完成小組作業,大家都說我「人很好」。其實我並非刻意為之,而是修煉使我自然而然成為更好的人,也讓我在講真相時更容易被理解和接納。」Cyrus說。
拋開恐懼 講出真相
曾經,Cyrus因為恐懼而不敢與人談起法輪功。但大學期間,他開始主動向室友講述迫害的真相,並耐心回答他們的疑問。發現講真相並不如想像中可怕,反而讓他感受到人的善念仍在。同學們雖對中共的行為各有看法,卻大多能認同法輪功是無辜受害的。
後來,Cyrus利用寒暑假及週末回去找初中、高中的朋友,講述真相,也勸他們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保平安。「大家都說我變了,變得自信、善良、陽光,而我則真切看到人人都有善念,人人都有佛性。」
然而,迫害並未因Cyrus的長大而停止。大二時,Cyrus因使用同學提供的翻牆工具而接到來自家鄉的警察威脅電話,這讓他意識到安全風險。後來,他轉用由海外法輪功學員開發的「自由門」軟件,雖然速度較慢,卻讓他更安心地閱讀被封鎖的資訊與歷史真相。
逃離母國 不忘使命
中共的騷擾如影隨形,父母每逢「敏感日」都會遭遇突然搜查與電話威脅。Cyrus也曾在搭乘火車時被帶走搜身。
那是在2021年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Cyrus在第一次出差抵達車站時,他與另一名乘客被點名帶走搜身、檢查行李。「這次甚至連行李箱的內襯都撕開檢查,他們強行索要我的手機、電腦密碼,之後連上他們的設備仔細檢查。」
Cyrus反覆問他們問什麼這樣對他,回答說是因為你們家修煉法輪功。由於Cyrus電腦裡保存有大量揭露關於中共迫害的真相內容,他們把Cyrus強行帶到了審訊室讓他坐上審訊椅。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我有點懵了,我努力恢復正念和理智,避免被他們套話,儘管他們多次威脅我要把我送進監獄關幾年,我也沒有暴露任何別的同修,保持理智。後半夜時我已經筋疲力盡,他們看到我犯困便會大聲拍桌震我,恐嚇我,最終他們沒有從我這得到什麼想要的信息,也沒有證據證明我有傳播真相視頻,便以『訓誡』的名義,在第二天中午放了我。」
這場風波後,Cyrus與家人商議,決定離開中國。2022年,Cyrus赴日留學,在課餘時間參與當地法輪功學員的講真相活動。「無論是街頭發資料、舉橫幅還是大型遊行,我都積極參與,期盼更多人能看清中共的謊言與邪惡,幫助仍在大陸受難的同修少受迫害。」

Cyrus已身在海外,但中共對他家人的迫害仍未止息。2023年9月,警方闖入Cyrus父母的出租屋,搶奪鑰匙、強行搜查,並帶走他的父母到派出所單獨審訊,強行打開他們的手機檢查後,雖未查獲任何證據,仍口頭威脅「不准再修煉」。
此外,每逢「敏感日」,他們會半夜敲門、隨機搜查、打電話騷擾。甚至Cyrus不修煉的姐姐,也遭受警察不斷騷擾與威逼利誘,要求她提供我們的下落與情況,對她的生活造成極大干擾。
2024年,Cyrus前往美國繼續深造,並持續參與講真相活動。「自從1999年7月20日中共正式開始迫害法輪功,轉眼已經26年,我也從蹣跚學步的孩童,成長為了大人。我的青少年時代從迫害中走來,是無數個法輪功學員家庭的縮影,僅僅因為我們信仰『真、善、忍』。」
時值7.20反迫害26週年之際,Cyrus想借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說出自己的心聲:
「今天的我,有幸能在自由的國度說出真話。但這場迫害仍在大陸持續發生,父母曾在獄中遭受的酷刑無法一一詳述,許多同修的悲慘經歷也無法盡錄。
「昔日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只剩下斷壁殘垣供人追憶,被迫害三百年的基督教文明卻傳遍世界。自古邪不壓正,這場迫害終將結束。願您了解真相,明辨是非,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選擇良知與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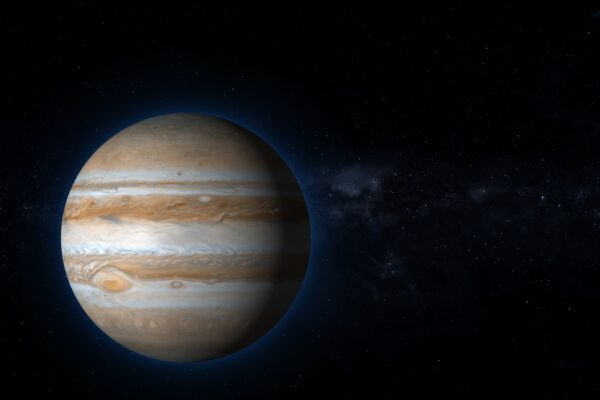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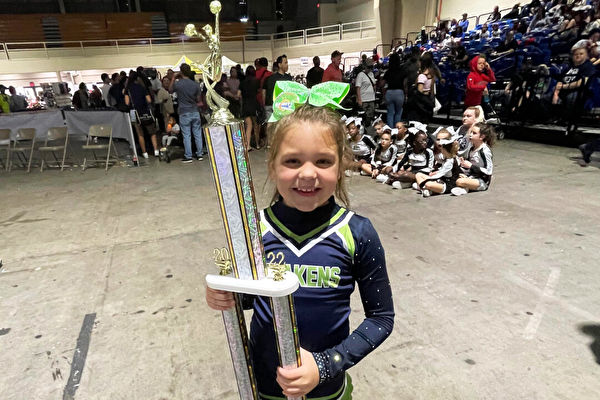







修炼易,在大陆不易,修炼难,在大陆难上加难。感人的故事,不屈的修炼人,大陆多少修炼家庭的写照。
[3]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