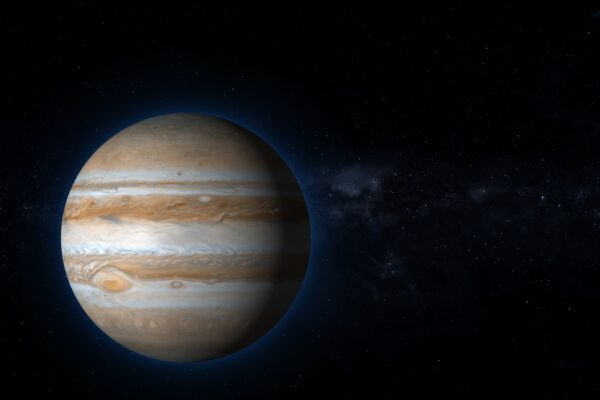太平洋邊,雨季的舊金山北灣。午後時分,海鷗點點,白雲舒卷。沒有風,自然波瀾不興。柔韌的天光在水面上慢慢展開,一層一層,半夢半醒的樣子。

呂遊銘先生畫筆下的貓。(呂遊銘先生提供)
長橋若虹,市聲漸遠。再往前走,水光退去,山路婉轉。那些山,高的並不突兀,卻纏纏綿綿。坡緩,林深,樹影交錯, 紅的紅、黃的黃、各色沉沉的綠,在秋意裡彼此交映。山路很窄,一會左,一會兒右,不見行人。落葉成陣,唯有鳥聲。路邊人家三三兩兩,沿路都是籬笆。非鐵非木 ,只是各色小樹自然生成,高一些的花花草草,從院子裡探出頭來。
曲徑數轉,人家始現。我今天所要探訪的畫家呂遊銘先生,住在這僻靜的山下。前院不大,一棟看似尋常的兩層小樓。大大小小的樹圍著,葉大如蒲扇,一地綠草,夾雜著野花。
進門
門一開,畫先迎人。牆上、地上,畫多得近乎不講秩序。大幅小幅,彼此倚靠,像各自佔了一段光影。
女子的臉,線條誇張,卻帶了幾分溫婉。
雲在天上流動,水在遠處閃光,莫內的痕跡若有若無。不是臨摹,而是記憶。
金門大橋橫在色塊之間。船帆,大海,彼此呼應。 彷彿加州的日光被拆散了,一點一點,落在畫布上。
一樓客廳整個空間都像在閃爍。
他畫的山,是紅色的。 顏色厚重。在夕陽裡靜默。
呂先生家裡的畫,貓最多。牆上有,地上有,洗手間也有。大小不一,姿態各異。
有的目光清明,有的帶著幾分自得。有蹲的,有坐的,有伏在橋上的,也有懸在高處,目光灼灼,彷彿正俯視來人。
樓梯間,一個女孩騎著貓在飛。並不突兀,反覺自然。
角落裡,還有兩幅早年的60年代台北集市造景圖。人群熙攘,卻不喧鬧,像記憶深處的聲音。
我站在那裡,一時不知──是走進了一個人的居所,還是誤入了一個另外的時空。
貓
貓,是呂遊銘畫裡最久、最深的母題。
他們常在室內。爐火旁,床邊,窗前。
不是戲劇場景,而是生活本身。他們不是被觀看的動物,而是進入畫中的角色。
有性情,有重量,有敘事。
畫面安靜, 卻不空。 像夜裡有人坐在你身邊,不說話,卻讓你知道── 你被看見。
呂先生說,這些貓,不是想像出來的。
呂太太說的故事
說到貓,呂太太先笑。她說,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婆婆給五歲的孩子買了一隻貓。從此,就是一生的緣分。
家裡一直有貓。他們在屋裡走,在屋頂曬太陽,在窗前睡成一團。
後來,夫妻倆經常要去各大洲旅行,路太遠, 時間太長。捨不得把貓送去寄養。於是,只好不再養了。
說這話時,她語氣很輕。像在說一段
已經放進心裡,卻從未離開的日子。

呂遊銘先生畫筆下的貓。(呂遊銘先生提供)
貓王
為什麼畫那麼多貓?為什麼你畫貓總是畫那麼大?
呂先生說,他曾經有一隻橘紅色的虎斑貓王。年輕時, 伏在鄉居屋頂, 享受即將消失的夕陽。
到了老年,不再跳躍。身體變得沉重。
存在本身,就有了重量。
天際傳來了噴射引擎聲,波音707巨大機影低空掠過。貓王隨著轟鳴聲轉頭望,不自覺的低了一下頭。貓王覺得它自己是巨大的,大到足以被飛機壓到。
呂先生說,正是那時,他開始真正學會用貓的角度看世界。
貓的腦子很小,卻彷彿明白──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大於一切。

呂遊銘先生畫筆下的貓。(呂遊銘先生提供)
禁止畫畫
呂遊銘的童年,是被「禁止畫畫」的。
60年代初,他還只是個國中生 。那天,正埋頭畫著漫畫, 一群同學圍著看。笑語喧嘩間,課桌邊有個小孩不慎跌倒。這個小小的意外換來一張嚴厲的「記過單」。
在那樣的年代,秩序比事實更大,服從比童真重要。一個愛畫畫的孩子,就這樣被貼上「不安分」的標籤。某日看到一位同學挨了一串教鞭,呂遊銘氣不過,作了一幅素描:老師高舉教鞭,孩子畏縮地舉著雙手。還寫下一行童稚的小字:「揍人為快樂之本」。像在沉悶空氣裡點燃的一根細小火星。圖畫在同學間飛快地傳閱,於是,他被學校正式禁止作畫。那一年,他第一次知道── 原來畫畫,是會「惹事」的。
一個被按住的孩子
1950與60年代的台灣,是一個一切講紀律的時代。校園裡,統一、安靜、整齊是首要條件;
大人們追求可預測的未來,不喜歡孩子「亂塗亂畫」。
對老師來說,他的畫太跳;
對家人來說,畫畫沒出息;
對社會來說,「圖像太容易引起誤會」。
多年後,他在紀錄片《童夢》裡說:
「很多年一直做噩夢,人家在追我……我又不是真的犯罪,可是我的罪名很重。」
一個孩子最深沉的恐懼,不是懲罰本身,
而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而創作本身,也許就會成了罪名。
那是一個功利主義的時代,只要不是經世致用的東西,都是吃不飽飯的雕蟲小技。後來進入復興美工,經過良師斯巴達式的訓練,他的藝術才能開始顯現。
他幫楊牧、朱天心、林良等人畫插圖,
出版過二十多本童書插畫,
在報紙副刊長期繪圖。
但即便如此,他仍習慣「低調」。
不炫耀、不張揚、不放大。
不是謙虛,而是——
在那個年代,太亮的光也會帶來危險。
他的筆觸克制,作品盡量平和,
連色彩都避免太高調。
他在學會畫畫之前,
已經先學會了「如何不被看見」。
戒嚴時代帶來的恐懼
呂遊銘發現自己設計的室內作品被放進教科書,作為與對岸破屋的對比材料, 成為政治宣傳的一部分。
那是一個創作者無法決定「自己作品會被如何使用」的年代。
他忽然意識到:畫畫不是創作,而是一種揭露。一種可能隨時被誤解的風險。
為了自由呼吸
33歲那年,他決定移民美國。那時候,他已經成了家,開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不錯的收入。拋開一切, 只是為了找一個嚮往了很久的遠方。
他後來形容那段日子:
「像第一次呼吸到沒有警告味道的空氣。」
在美國,沒有人問他畫的「意義」;沒有人盯著他的色彩;沒有人告訴他「這樣不安全」。
沒有門派之爭,沒有玻璃帷幕牆。他第一次感到:畫畫真的可以隨心所欲。
自由在畫裡長大
遷居美國之後,他的畫像是突然鬆開了繩子。色彩變亮;筆觸變軟;線條變快;
畫面開始奔跑。
最早的時候,畫面裡只有城市、屋頂、街道、窗戶。世界很完整,卻沒有多餘的位置。
後來,貓出現了。不是突然跳出來的,
而是像一口憋了很久的氣, 在某個時刻,終於被允許呼出來。
貓不是被訓練出來的動物。
它不需要口令,不等掌聲,也不向任何人解釋行程。 它只遵循身體的感覺: 該走的時候走,該停的時候停。
那隻巨大、慵懶、無所不在的貓。大到屋頂容不下,大到城市像玩具,大到雲必須讓開一塊空白。
那隻貓:
蹲在巴黎鐵塔頂部
在紐約時代廣場伸懶腰
跨過台北101樓
城市變得小小的, 貓——卻大得異乎尋常。
這不是誇張,而是一種心理的平反。
一個曾被世界壓小的孩子,終於有能力把世界縮回他所能掌握的大小。 讓曾經壓在頭頂上的一切都倒過來重新排列。
山中結語
日將西斜,暮色沉沉,山影被墨色熏染成不可見。
我離開時, 回頭看了一眼那棟小樓。
樹影覆在牆上。隱隱透出的燈,就像老貓睡在沙發上的溫柔時光。
我忽然明白──貓就是呂遊銘的化身。是那個曾被追趕,卻終於學會靜靜坐著、
安心呼吸的自己。
這一趟,我來找呂遊銘。卻更像是——
被北灣的水光,被肯特菲爾德的山,
被一隻沉默的貓,慢慢引到這裡。此刻,山睡了,貓也睡,夜色歸於安寧,我不禁慢慢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