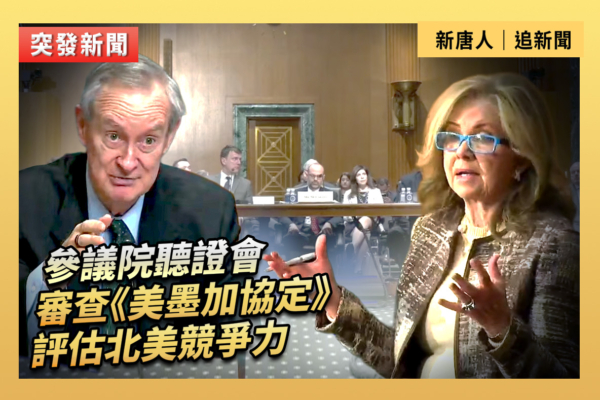【2025年07月21日訊】本集我們要來談一個有點敏感,卻又是每個人幾乎都不可避免的話題,那就是跟父母一起同住的選擇。當然這有很多種情況,有些人不需要和父母同住,但是對有些人來說,卻不得不和父母同住。對華裔族群來說,和父母一起住,可能有親情、孝道和義務上的需要。不管如何,本次我想從和父母同住這個角度聊聊美國房地產。
與父母同住還是搬離?
以前的我們還年輕,父母健康也還可以自如行動。但是,當我們也漸漸進入中老年,父母的健康自然更不如從前。以前我們會想要出去闖一闖,儘早脫離爸媽,開創自己的人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回過頭來,我們可能會發現,父母還在原地等著我們,他們逐漸需要我們的幫助。
當然,給父母幫助,不一定就是住在一起,有可能是固定的探視、金錢上的支出、各種能力上的幫忙等等。尤其身在美國,父母可能是移民的第一代,對美國社會的各種障礙肯定會比較大,例如醫療服務、各種補助申請、開車交通等等。
在東西方文化,自然都有這種親情的牽絆,只是在中國的文化裡面,我們特別講究孝道、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道德和義務,所以這種家庭同住的現象會比其他族裔來得明顯。
不過,現代的獨立意識比以往的世代都來得強烈,年輕一代多數都會想要有獨立的生活,尤其婚後有了家庭、孩子,兩代人的生活方式逐漸差距很大,飲食、作息、教育和價值觀等各種方面都有落差,如果要住在一起,或許會面臨極大的居住考驗。
所以,不管是本來就和父母住在一起,考慮搬出去;或是已經在外居住,考慮搬回來,兩種情況的人可能都很煩惱,到底該怎麼做決定。
在你們做出決定之前,以下我們就來看看美國有多少人和父母居住,在不同年紀、不同族裔都有不同的比例。
不和父母住=不孝順?|在美國和爸媽住=失敗?|和父母同住 3大主因 4點大優點|華裔子女的困擾|適合多代同堂的房型 #美國地產熱點 7/19/2025
現在美國有多少人和父母同住?
根據2024年美國人口普查資料,約57%的18~24歲年輕人與父母同住,沒有意外這是最大比例的群體;約18%的25~34歲成年人住在父母家,這個年紀的群體,比例瞬間下降,不難理解多數人到了這個年紀,已經要外出工作,所以多數都搬出家獨立生活。
到了35歲以上,和父母同住的比例更少了,只剩下5.9%,換句話,100位35歲以上的美國成年人,僅有約6位與父母同住。其實在35歲以上的年齡段,數據已經沒有提供精確的分齡,直到65歲以上,比例幾乎是零,因為父母一般都已經過世了。因此,從數據看來,美國人尤其到成年以後,僅有非常少的比例和父母同住,即便到了父母比較年長的時候,比例還是很低。
在從族裔來看,根據2021年皮尤研究的數據顯示,約29%的25~29歲的亞裔成年人與父母同住,遠高於白人同年齡層的18%。沒有意外,亞裔擁有最高的比例,等一下我們再來分析背後的原因。
在西班牙裔、拉丁裔,約26%~28%的25~29歲族群與父母同住。可能的原因是,拉丁裔的家庭向心力較強,傳統文化支持多代共居;加上家庭收入中位數可能略低,也促進合住的情況。
再來看非裔美國人,與父母同住的比例亦偏高,但略低於亞裔與拉丁裔,該年齡段約24%的成年人與父母同住。
白人是與父母同住比例最低的族裔,只有約18%~20%,傳統上白人較重視獨立生活,所以離家年齡相對較早。
為何要和父母一起住?三大主因四大優點
為何和父母同住?研究中指出三個主因是,一、文化價值觀:亞洲與拉丁文化中,多代同堂是常態或被視為孝順的表現;二、經濟因素:族裔間的薪資與財富差異也影響搬離家庭的能力;三、居住地區:居住在高房價地區,如加州、紐約市的少數族裔,更可能與父母同住,否則單獨居住的成本太高昂。
其實現在高房價時代,與父母同住的比例也有升高,尤其在疫情之後,通脹嚴重、生活成本問題和健康問題,導致和父母同住增加,在美國主流社會中沒有那麼羞於見人,相較數十年前有顯著的增長。在美國1960年代,僅約有7%~11%的成年人和父母同住。
和父母同住 在現代還有幾個優點:
1. 節省金錢:這有多個方面,其一是房租支出降低,可省下住房、水電、網路等生活成本,有助於儲蓄、還債、投資或為購屋準備首期。另外一方面,現代的長照機構的費用越來越高,許多家庭其實負擔不起,如果子女願意負擔起照顧責任,對兩代人來說確實會省下大筆資金。
2. 家庭支持:父母和子女可獲得情感支持與生活照應,如生病、工作壓力時的慰藉。若生了孩子,祖父母更能幫忙照顧,增進祖孫情之外,也節省托育費用。
3. 照顧父母:便於就近照顧年邁的父母,減少他們孤單、就醫不便等問題。通常多代同堂就是一種孝道的展現,或家庭凝聚力的表現。
4. 文化傳承與情感連結:促進與長輩的交流與文化價值觀的傳承,特別對亞裔、拉丁裔族群來說很重要。
為何不和父母一起住?華裔子女困擾
和父母一同居住,固然很好,但還是有許多「不願意」的原因:
1. 缺乏隱私與個人空間:兩代人的生活習慣差距很大,容易造成摩擦。年輕一代難以有自己的社交、戀愛或休息的空間。
2. 代際衝突:在教育觀念、理財、作息或飲食等方面都可能產生衝突。尤其當雙方都是成年人,對「誰當家作主」常有模糊地帶。如果有了孩子,年輕一代對孩子的教育理念肯定會不同於上一代,特別是在西方長大的孩子,相對華人文化成長起來的上一代,在各方面的差異都極大。如果想要住在一起,雙方都要有很清楚的認知,和可以妥協的空間。
3. 降低獨立性:同住也可能導致孩子延後獨立思考,與生活能力的建立。尤其在西方文化中,有時將與父母同住視為「未脫離父母」,可能會被同事嘲笑。
另外,對美國華裔而言,要不要與父母同住,更有以下一些常見的困擾:
1. 文化價值衝突:孝道與個人自由的拉扯,在傳統華人文化中,「與父母同住、照顧父母」被視為孝順。然而,在美國主流文化中,成年後獨立自主是普遍預期,與父母同住經常被視為「不成熟」,甚至是「失敗」的表現。所以,華裔子女常處於這兩種價值觀之間,可能產生內疚或矛盾的心理。
2. 私生活受限:華人父母常有較強的參與或控制慾望,可能會干涉子女的飲食、交友、甚至職涯選擇。華裔子女即使成年後,仍與父母同住,也常被父母「視為小孩」,導致缺乏完整自主權。在華人家庭中,成年子女還讓父母照顧、準備三餐的情況非常普遍,父母也熱衷於此。相反,如果子女不願意被父母照顧,還可能被當作不孝順的表現。
3. 婚姻或親密關係受影響:與父母同住可能讓談戀愛、結婚或建立自己的家庭空間變得困難,尤其若父母不願放手或過度干涉,都會導致孩子婚姻受到影響。中國有句俗語:「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確是有道理。不過,過度關心,不敢讓孩子放手飛,不可否認也是一大問題。
和父母住有哪些適合的房型和社區
經過以上的考慮,如果您打算和父母一起住,或者和自己的兒女同住,這時候有幾種房型會非常適合兩代人或三代人同住,畢竟有好的住宅條件,在客觀條件上,更能避免一些生活上的摩擦。
1.雙主臥設計:父母與子女各自有完整主臥與衛浴,避免共用造成不便。2.一樓臥房或套房:適合年長者行動不便,無需上下樓梯。3.獨立出入口或ADU(附屬住宅單位):保障雙方出入隱私。
4.開放或封閉式廚房:視家庭習慣與飲食調整,假如以父母下廚為主,或許可以考慮中式的封閉廚房。5.充足的公共空間:例如雙客廳、家庭娛樂室、寬敞餐廳,讓彼此都有適當的休閒。6.可擴充空間:如果房產有可地下室、閣樓、或後院能增建ADU都是非常理想的,以便日後想要打造另一個活動空間,或居住的彈性。
對於外部環境來說,社區的選擇也很重要,尤其有疾病在身的父母,最好選擇靠近醫療機構,方便就醫或處理緊急的健康問題。還有交通問題,是否靠近高速公路、公共運輸,讓老年人容易購物、自由外出方便。
治安也是要好好考慮的因素,尤其是老人白天常留家中,治安良好格外重要。像是前陣子,某些社區經常有專門針對華裔年長者下手的罪犯,搶走錢包、車子,甚至暴力攻擊等,都令人感到憂心。
還有社區的友善程度也要考量,是否有老人中心、公園、步道等休閒設施,讓老人隨時可以到戶外運動、散步也非常重要。
和父母住有哪些稅務優惠?
最後,我們來看看在政府的政策方面,有些能對年長者提供更多的優惠。例如在加州2021年正式實施19號提案,對年滿55歲以上的屋主提供稅收優惠,在他們選擇搬家後,仍可攜帶原房屋的低稅基(Assessed Value)到新房產。
過去這項稅務優惠,僅限於加州部分縣市、而且只能搬一次家,現在19號法案全加州適用,可搬家最多三次,也不再限制新房產的房價是否同價或更便宜,但如果新房價比原房產價格更高,也只要補繳差額稅。
對想與父母同住的人來說,會讓老年父母願意搬家,而不用擔心房產稅暴增,是鼓勵代際同住的重大政策之一。
此外,聯邦層級對照顧年長父母也有一些稅務優惠,比如可將父母列為受扶養人,享有稅額抵免與稅務級距調整;支付的醫療費用、照護支出也可以選擇抵扣,減輕子女的經濟壓力。◇#
責任編輯:李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