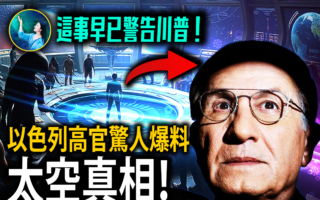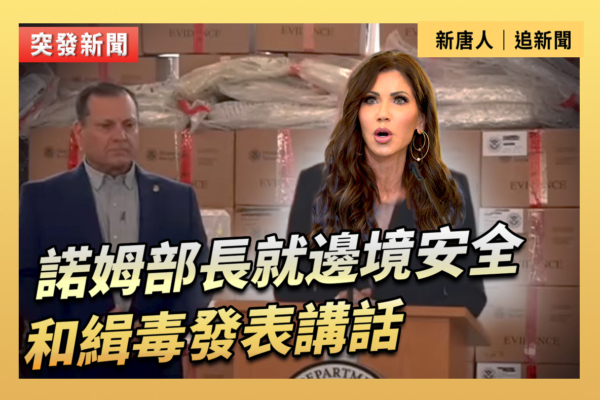大家好, 我是扶搖。歡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謎。
6月13日,大家還在熟睡的午夜時分,突然——轟!以色列先進戰機像利劍一樣劃破夜空,導彈精準命中目標,伊朗的核設施、空軍基地……瞬間變成火海。這場突襲來得太快、來得太猛,震撼整個中東,也讓全世界跟著倒吸一口氣。
今天,我們就帶你來聊聊這場以伊衝突背後的驚人故事。
核戰後果多可怕?
以色列稱,此次行動的原因是,伊朗手上的濃縮鈾已經足夠造多顆核彈!再不打,短期內核彈就能做好。到那時候,不只是以色列,全世界都要提心吊膽!
如果多顆核彈引爆,雖然還不至於把地球炸個粉碎,但後果是災難級的。根據科學家的說法,這種爆炸會引發「核冬天效應」,導致全球氣溫急速下降,植物難以生長。地裡長不出莊稼,全球幾十億人都會餓肚子!
這「核冬天效應」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等等我會幫大家詳細拆解。
我們再往下挖一層:為什麼伊朗敢這麼囂張,冒天下之大不韙,偷偷製造核武?因為它背後有兩個核大國撐腰——俄羅斯和中共國。如果伊朗真的敢發射核彈,以色列一個國家可能頂不住,到時候誰會介入?沒錯,就是美國。可美國一旦出手,伊朗背後那兩位老大哥會袖手旁觀嗎?當然不會!那麼,很可能會出現三個核大國開打的局面。
到那時候,我們面對的將不只是什麼糧食危機,而是,人類的集體滅絕。這可不是我在講恐怖故事唬你,這是科學家根據真實數據發出的警告。
恐龍怎麼死的?
知道恐龍怎麼滅絕的嗎?小行星撞地球?嗯,說對了一半而已。
撞地球的那顆小行星,直徑還不到15公里,沒有把地球撞歪,也沒有把地球撞出軌道。就純粹從撞擊力來看,影響其實沒那麼大。真正讓恐龍滅絕的,是粉塵。就是那種細小、輕飄飄、你平常根本不會注意的塵埃。
撞擊之後帶來大量的岩石粉末,這些細小的粉塵總重量達10億噸,在撞擊瞬間被震飛到超高空,大氣層的同溫層,也就是離地面十幾公里高的地方。那裡的氣流非常穩定,粉塵一進去就像被封印一樣,一待就是好幾年,而且還會慢慢擴散,最後覆蓋整個地球。
結果會怎樣?
陽光被擋住,地球陷入黑暗,因為缺乏光合作用,陸地上的植物和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大量死亡。那些以它們為食的動物們都餓死了,處在食物鏈頂端的恐龍也難逃一劫。
所以,可憐的恐龍啊,不是被小行星撞死的,而是餓死的。
核冬天效應
如果說,這個6,500萬年前故事太過遙遠的話,我們再來看一個200年前的故事,一個真實發生過的故事。
1815年4月,印尼坦博臘火山大規模噴發,大量火山灰飄向高空。
那年秋天,地球北半球的光照量只有平常的25%。第二年夏天,也只有40%。結果,歐洲、北美都迎來了歷史上最詭異的一年——「無夏之年」!許多地方氣溫創下新低,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六月飛雪。
隨之而來的,就是糧食問題。在北美,小麥和乾草價格飛漲,在歐洲,出現遍地飢荒,最後導致20萬人死亡。
核爆炸產生的塵埃和濃煙,比火山灰更毒、更濃、更持久,那麼,後果會有多可怕?
然而,關於這一點,很長一段時間都沒人注意。1975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還發表一份報告,說在一場核戰爭之後,不會出現長期的危害性氣候或對生物的不利影響。
直到1983年,五位來自美國和西德的科學家組成了一個研究小組,叫做TTAPS小組。
他們把1816年的「無夏之年」和模擬的核戰資料放在一起進行計算,結果發現,如果真的打起核戰,天空會被煙霧遮住,陽光無法穿透,跟恐龍當年的遭遇一樣,大地會變成冰窖,動植物將出現大量死亡,人類能否能倖存只能看天意。
他們把這種現象定義為「核冬天效應」。
1983年10月31日,華盛頓召開了一場重量級的會議,來了五百多位國際頂尖科學家,還有蘇聯的專家遠程連線。大家一起重新演算TTAPS小組的數據。結果怎樣?無懈可擊!
所有人都震驚了!
因為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地球上的下一場生物大滅絕,很可能將來自於一場核戰。人類會自己滅絕自己。
這,就是1980年代最重磅的一個預言,也是今天各個超級大國那麼重視核武器的原因。
核戰,千萬不能打。一次都不能。
那麼,以色列的轟炸能起作用嗎?核戰危機最終會解除嗎?
我們不妨來聽聽預言家怎麼說。
網紅預言家是怎麼說的?
早在幾個月前,兩位網紅預言家,比格斯和帕克,就不約而同預測到了這場危機的來臨!
川普剛上台,比格斯就放話說,川普將「如同獅子一般,揮舞著鞭子」打擊伊朗,從經濟上掐住咽喉,從軍事上阻止伊朗發展核技術。
而且他還說,美國會發動一場快速又致命的軍事行動,用上一種從來沒在實戰中曝光過的祕密武器!
結果呢?還真讓他說中了!
6月21日,美國不動聲色、出人意外地參戰,一舉轟炸了伊朗三個最關鍵的地下核設施!這次行動中首次亮相的那款祕密武器,就是GBU-57巨型鑽地炸彈!
這種炸彈是美國獨有的武器,能穿透地下60米的土層,爆炸威力比目前威力最大的炸彈,俄羅斯的「炸彈之父」還大3倍。在目前來講,還沒有對手。
事後,美國總統川普信心滿滿地說,伊朗重要的核濃縮設施已被徹底摧毀,現在他們必須同意結束這場戰爭。
那麼,核戰的風險,真的就這麼被化解了嗎?
帕克說,不一定。
戰爭肯定會結束,但和平,還早。
事實上,早在去年,帕克就預言美國和以色列一定會聯手打擊伊朗核設施,而且斷言以色列會先出手。事實果然如此。
6月13日,以色列的襲擊剛發生,帕克當天就上傳影片,分享他看到的未來。
他說,他看到在一個小鎮附近,有一個大型核實驗基地,有大約3萬名核科學家和工作人員在那裡日以繼夜地趕工,製造核彈。
所以,以色列的判斷沒錯,伊朗一直都在否認,說自己沒有祕密發展核武,但他們其實一直都在撒謊。
雖然這次轟炸取得重大成果,但帕克警告說,戰爭不會這麼快結束。
因為俄羅斯和中共國會在暗中幫助伊朗。所以,這場戰爭將演變成為一場更大、更廣泛的戰爭。
伴隨而來的,就是油價大幅上漲,股市受重創,世界經濟出現動盪。說到這,帕克還重點提醒,說加密貨幣不再是安全避風港了,大家千萬小心。
不過好消息是,這一連串的混亂不會拖太久,和平將在2025年底前到來。
和平來自內部
但真正讓中東回歸和平的,不是外部壓力,而是伊朗人民自己。
他看到伊朗內部將爆發一場高層暗殺行動,目標就是推翻現有政權。
暗殺有沒有成功帕克沒有說,但他說,伊朗的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將消失,有官員會逃亡到土耳其。一位謎一樣的女子會出現,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領導者,有著強烈的藝術家氣質。
最後的結果是,伊朗將發生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最終建立一個新政府。
帕克說,在那個未來的畫面裡,人們走上街頭,高舉著紅色和黃色的旗幟。那不是現在伊朗的國旗,而是像過去王室時代的傳統旗幟。
這象徵著:伊朗將走向復興、回歸傳統,邁向民主。而在那之後,伊朗的未來,將會一片光明。
說到這裡,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其實現在這個獨裁又壓抑的伊朗,在1979年之前,完全不是這樣的。
白色革命
那時候的伊朗,其實是一個開明又現代的民主國家,和美國、以色列的關係都很好,人民過得富足又自由。
當時統治伊朗的,是巴勒維王朝的國王,穆罕默德·巴勒維(Muhammad Rizā Shāh Pahlavi),一位具有現代思維的君主。
1963年,在美國的幫助下,他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普及、國有企業現代化等等,史稱「白色革命」。
這其中最有突破性的,就是賦予女性選舉權。在這張1963年拍攝的相片中,燙著時髦卷髮、穿著洋氣襯衫的伊朗女性,正開心地在投票。
那時候的伊朗經濟騰飛、國庫充盈,國外僑民紛紛回流,西方媒體一致看好,說伊朗會很快躋身世界一流強國。
然而這一切的美好,都在1979年1月戛然而止。
因為巴勒維的改革,雖然讓老百姓受益,卻動到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尤其是那些伊斯蘭教神職人員和貴族階層。
一個極具煽動力的人,霍梅尼,出來鼓動大家造反了。而且,他還很有市場。
1979年1月,霍梅尼策反成功,巴勒維國王被迫退位,流亡美國。
伊朗從此改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霍梅尼出任最高領袖。
霍梅尼剛一上台,就搞全盤伊斯蘭化。對外,跟美國和以色列斷交,對內,訂立一套極端的宗教法律,把人民牢牢鎖死。
很多人這才驚覺:完了,被套牢了。
但,一切都已經太遲。
直到2022年9月,一位年輕女子艾米尼(Mahsa Amini)因為頭巾沒戴好,露了一點頭髮,就在街上被「道德警察」活活打死。
這件事瞬間引爆了全國的怒火,引發一連串的抗議浪潮。但政府的回應只有一種,那就是鎮壓!
上街的民眾一個個被抓、被打,被消音。很多老人流著眼淚說:「悔不該當初啊,悔不該當初……」
而未來的希望,會不會正如帕克所說的那樣,從這片土地的人民內部重新燃起?
說到這裡,其實帕克在他的影片裡,不只是預言了未來,還特別花了很多時間,回顧伊朗歷史,向伊朗民眾喊話。
他說,你們真正的信仰,並不是現在這個極端的伊斯蘭教,而是拜火教(Zoruststerism),那是一個非常寬容的宗教。還記得你們的居魯士大帝(Cirrus the Great)嗎? 記得那段真正屬於你們的輝煌嗎?就是他幫助猶太人重建了他們的第二聖殿。
說到點子上了,伊朗人為什麼要為一個外來宗教去賣命呢?
拜火教與末日預言
其實伊朗人的祖先,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來自北方,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伊朗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雅利安人的土地」。
不過這個名字還是1935年才開始用的。在這之前,這片土地的名字叫做波斯。直到今天,很多海外伊朗人還堅持自稱是波斯人。
波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他們崇拜的是風、火、水、地四大元素中的火,因為火象徵光明與真理。所以,人們就稱它為拜火教。
帕克為什麼說拜火教非常寬容呢?因為這個信仰的核心就是「善」,教導民眾要做到三個「善」字:善念、善言、善行。所以這個宗教,也被稱為是「善良的宗教」。
拜火教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一位至高無上的神,叫做阿胡拉(hura Mazda)。阿胡拉是善的化身。跟阿胡拉對立的,是毀滅之神安格拉(Angra Mainyu)。安格拉是邪惡的化身。
這個世界在剛被創造出來的時候是完美的,但後來被邪惡腐蝕。善與惡之間將展開一場長達三千年的對決,最終,善將戰勝惡。
到時候,救世主薩奧希揚特(Saoshyant)將降臨人間, 讓所有的死者一一復活,進行審判。每個人都將穿過一條金屬熔化的河。對正義的人來說,它就像一條溫暖的牛奶河,很容易就能蹚過去。而對於惡人來說,那條河就是地獄,因為他們會在河水中被焚燒。
這條河會一直流向地獄,在那裡,它將毀滅邪惡之神安格拉以及宇宙中最後殘留的邪惡。一切都將被淨化。世界最終將恢復到創造之初的完美狀態。
這個預言,跟聖經啟示錄裡的末日預言是不是很像?
沒錯,很多人都發現,世界各地的古老宗教,都有非常相似的末日預言。也許這些古老的神話,其實只是從不同角度,在描述同一件事,那就是末日大審判。
居魯士大帝與聖殿重建
說完信仰,那麼帕克提到的居魯士大帝,又是怎樣一位英雄呢?
你知道嗎?2600年前,在他的領導下,波斯帝國橫掃歐亞非三洲,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大軍所到之處,沒有一個國家不敢不臣服。
但居魯士不是一個殘暴的征服者,而是一位推行宗教自由、尊重民俗的仁君。
當他滅掉巴比倫之後,他把被關在監獄中的猶太人都放了出來,讓他們重返家園。結果,猶太人告訴了他一個預言。
他們說,150年前,先知以賽亞就已經預言會有一位叫「居魯士」的王出現,幫助他們回歸聖城、重建聖殿。
居魯士聽到這裡,忽然就莫名感動了。真的假的?150年前,你們就知道我的名字了?知道我要做王?那好,雖然我對你們的神一無所知,但我會幫你們實現預言。
他不但讓猶太人回國,還把聖殿中被巴比倫人搶走的寶物全部歸還,總共五千多件。
他過世後,他的兒子大流士,還從國庫裡出錢支付建聖殿的工程費用、提供獻祭用的牛羊。
猶太人對此感激涕零,給了居魯士至高無上的榮耀,稱他為「彌賽亞」,意思是神選之人。在聖經中,被冠以「彌賽亞」頭銜的只有很少幾個人,像是耶穌,大衛王。而居魯士是其中唯一一個沒有猶太血統的人。
可見他在猶太人心中的地位有多崇高。
這也是為什麼,在歷史上很長時間裡,伊朗人,或者說是波斯人,和猶太人一直都相處融洽、彼此尊重。
帕克專程花時間講這段歷史,或許就是想提醒伊朗民眾:你們原本是自由的、開明的,有光明信仰、有輝煌文明的一群人,如今卻被極端政權綁架,背離了自己的根。
帕克是個真正愛好和平的人。他不只對伊朗有話要說,對中東最棘手、最敏感、也最危險的問題——第三聖殿的重建,也提出了一個充滿希望又非常美好的解決方案。
要知道,自從以色列復國之後,中東戰火一直延綿不絕,說到底,終極的火藥桶,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猶太人的聖地,也是阿拉伯人的聖地。猶太人在這裡建過兩次聖殿,但又兩次被毀。根據聖經預言,末日到來之前,猶太人將重建「第三聖殿」。
然而,等猶太人好不容易奪回耶路撒冷,聖殿遺址的正中央,已經矗立起一座宏偉的清真寺,也就是伊斯蘭教的「圓頂清真寺」。
要重建聖殿,就得拆毀清真寺。但如果拆毀清真寺,全體阿拉伯人都跟你沒完。所以,直到今天,以色列都遲遲不敢動手。
但帕克說,他看到的未來,不是戰爭,而是和解。
他說,當和平時代真正來臨時,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彼此和平相處,聖殿也會被重建。這或許還很遙遠,但帕克堅信,那一天,終會到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也希望「核冬天」永遠不會發生,如果您也相信和平是我們共同能創造的未來,那麼,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吧。
因為世界和平不是一句響亮的口號,而是靠你、我,我們每一個人,用心來守護。不是嗎?
未解之謎,我是扶搖。我們下回見。
歡迎訂閱YouTube頻道:https://www.youtube.com/@WJZM-FY
訂閱頻道Ganjingworld頻道:https://www.ganjing.com/zh-TW/channel/1eiqjdnq7go2dgb6zFtQ9TYK11080c
訂閱未解之謎Telegram群組:https://t.me/wjzmchannel
【未解之謎】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方沛#
var scripts_to_load = [];
var contentObj = document.getElementById(“epoch_socail_span”).parentElement;
var iframes = contentObj.querySelectorAll(“iframe”);
if (hasStorage && localStorage.getItem(“EpochOnetrustActiveGroups”).indexOf(“C0005”) > -1) {
if (iframes.length > 0) {
iframes.forEach(function(iframe) {
var dataSrc = iframe.getAttribute(“data2-src”);
if (dataSrc) {
iframe.setAttribute(“src”, dataSrc);
iframe.removeAttribute(“data2-src”);
}
});
}
var fvIframe = document.querySelector(“.video_fit_container iframe”);
if (fvIframe !== null) {
var srcURL = fvIframe.getAttribute(“data2-src”);
if (srcURL !== null && typeof srcURL !== “undefined” && srcURL.length > 0) {
fvIframe.setAttribute(“src”, srcURL);
fvIframe.removeAttribute(“data2-src”);
}
}
} else {
var atag = ““;
var hint = (encoding === “gb” ? (“(根据用户设置,社交媒体服务已被過濾。要显示内容,请”+ atag +”允许社交媒体cookie。)”) : (“(根據用戶設置,社交媒体服务已被过滤。要顯示內容,請”+ atag +”允許社交媒体cookie。)”));
if (iframes.length > 0) {
for (var i = 0; i 0) {
for (var i = 0; i < tweets.length; i++) {
var iTag = document.createElement("i");
iTag.innerHTML = hint;
tweets[i].appendChild(iTag);
}
}
var fvIframe = document.querySelector(".video_fit_container iframe");
if (fvIframe !== null) {
var iTag = document.createElement("i");
iTag.innerHTML = hint;
var parent = fvIframe.parentElement.parentNode;
if (parent) {
parent.insertBefore(iTag, fvIframe.parentElement.nextSibling);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