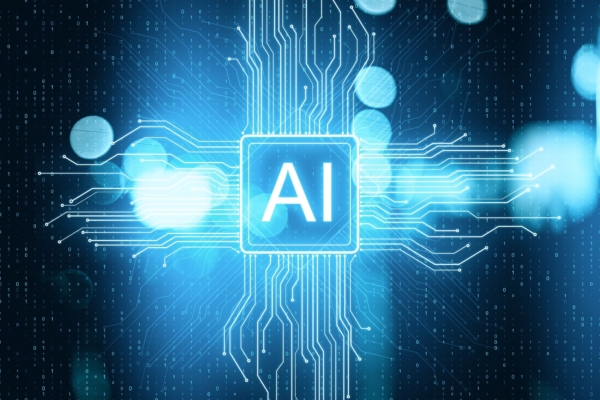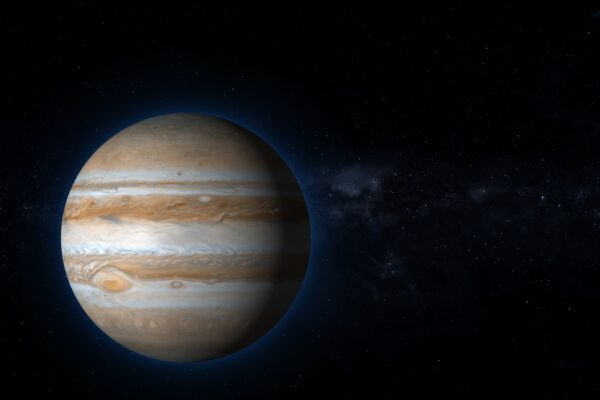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2023年11月11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Robert G. Natelson撰文/信宇編譯)自上月初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馬斯(Hamas)對鄰國以色列發動恐怖主義襲擊以來,令人驚訝的是,在美國校園內出現了大規模支持巴勒斯坦的力量,讓人不得不擔心,在被譽為象牙塔的大學校園裡,廣大學子們受到了多麼嚴重的思想毒害。
在本系列文章中,我將詳細解釋為什麼我們的大學正遭受著有毒文化病毒的侵襲,並且嘗試提出應對之道。
我為何關注大學問題?
讀者也許會感到困惑,我為什麼要不惜筆墨,對美國大學校園存在的種種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探討。
我與大學校園有著不解之緣。我曾在各種校園環境中學習和工作。我在一所私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我本有機會入讀更有聲望的公立大學,但果斷拒絕了,選擇在一所半私立半公立的大型大學就讀法學院,後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正確選擇,稍後會解釋這個決定的實際意義。此外,我還曾在一所州立大學學習希臘羅馬古典文學。
大學畢業後,我從事法律領域工作,期間曾在一所社區學院擔任兼職教授,後來又在一所大型州立大學和一所大型私立大學擔任兼職教授。
在學習了基本的教學技巧課程後,我曾短暫地擔任過社區學院的項目經理,並最終全職重返學術界。我先後獲得終身教職和終身教授職位,並在接下來的25年中一直擔任終身教授。我最初在一所小型私立大學任教,後來在一所中等規模的州立大學任教。我還擔任過一所大型州立大學的客座教授和一所大型外國大學的研究員。
我可以將學術界與其它行業進行比較,這一點是大多數教授無法做到的,因為我亦曾在私營中小企業工作過,目前還經營著一家諮詢公司。
大學從來沒有「學術自由」可言
作為象牙塔的大學一直被譽為誠實研究、不受約束地探索和表達競爭思想的天堂,事實上這只是人們的美好幻想而已。這個幻想在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1945—1990)廣為流傳,目的是保護同情共產主義事業的眾多學者。當時的想法是,極權主義的鼓吹者和其它傳統價值觀的批評者必須得到寬容和接受,因為「學術自由」是大學的核心價值所在。
我對這種理想有幾分同情,然而事實是,大學更多時候是主流觀念的堡壘,也是對任何不認同主流正統觀念的人不寬容的根源。
目前形式的大學是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歐洲發展起來的。它們是在宗教教派的支持下,與地方政治當局合作建立和運營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被要求遵守預先設定的宗教和政治規範。不信奉者被排斥或趕走。
事實上,一些被排斥或趕走的人也是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伽利萊(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在比薩大學(University of Pisa)不受歡迎,不得不搬到帕多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英國物理學家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不得不獲得王室豁免,以避免被迫加入英格蘭教會。法國籍物理學家瑪麗‧居里(Marie Curie, 1867—1934)在她的祖國波蘭亦被禁止接受任何學術任命。
去年11月,我在總部位於英國伯明翰市的《美國法律英國研究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American Legal Studies)發表了一篇題為「限制移民的權力與憲法定義和懲罰條款的原意」(The Power to Restrict Immigration 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s Define and Punish Clause)的研究文章,系統地了解了歷史上那些開創現代國際法領域的知識巨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與自己的大學或其它政治機構發生了矛盾,不得不逃亡到更合適的地方尋找生計。
即使在相對寬容的英國,正統(orthodoxy)精神也一直困擾著大學。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於1836年獲得特許之前,除非你是聖公會教徒,而且是男性,否則你就不能在該大學接受教育。
當然,長老會(presbyterians)教徒可以前往蘇格蘭接受高等教育,然而蘇格蘭的學校亦有自己的正統觀念。例如,在聖安德魯斯學院(College of St. Andrews,現為聖安德魯斯大學),每一位入學的學生都必須簽署一份宣誓書,表明自己信奉長老會,並承諾繼續信奉長老會。
因此,天主教徒、猶太人和女性在英國根本沒有大學可以選擇。
此外,由於英國大學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它們往往是國家特權的堅定支持者,與個人自由背道而馳。這一點現在可能聽起來很熟悉。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英國內戰期間,國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將牛津作為戰時首都。
受其影響,早期的美國大學也以特定的正統思想為基礎,所有人都必須遵守這些正統思想。
現代正統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的只是正統派的性質。學生和教職員工如果有幸能被「大學社區」接納,一旦公開反對正統信條,就會遭遇重重困難。去年2月,我曾在英文《大紀元時報》發表題為「最高法院應認識到『多元化』計劃只關乎左派政治而非教育」(Supreme Court Should Recognize ‘Diversity’ Programs Are About Leftist Politics, Not Education)的文章,文中詳細介紹了高校對其教師和管理人員強制推行正統觀念的一些方式。持不同政見者通常不會被錄用,在獲得終身教職之前就會被解僱,或者在獲得終身教職後被「揭發」,會受到其它不同方式的懲罰。
顯而易見,這些人往往是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在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我所在的大學系統有一個顯著的記錄,那就是學校以各種理由將持不同意見的學者趕走,而這些學者卻在其它地方聲名鵲起。
而倖存下來的持不同意見者被迫浪費寶貴的時間,接受「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等概念的灌輸。他們聽到自己的思想和他們國家的建國原則被肆意嘲弄。他們往往被避之唯恐不及,他們的資金被用來支持左派事業,他們無助地看著自己厭惡的意識形態得到官方體制的特別青睞。
我們不能縱容這些行為。當我還是一名法學教授時,我曾勇敢地支持財政上保守的事業,儘管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巨大的個人和職業代價。然而在更大舞台的社會問題上,我卻沒有勇氣挑戰正統統治。例如,我從未公開指出給予同性「婚姻」法律特權是一個愚蠢的決定。
這種謹小慎微的處事原則幫助我適應了這個社會。退休後,我親眼目睹了在我所在的大學裡,一位計算機科學教授因為表達了保守的摩門教(Mormon)婚姻和性觀點,而受到學校的不公待遇。雖然他的大部分觀點在幾十年前都是習以為常的,然而他現在卻不得不為這番言論而辭職。
令形勢雪上加霜的是,聯邦政府的強力干預加劇了左派的政治和文化偏見。聯邦政府為左派青睞的研究項目提供巨額撥款,這些研究項目包括環保主義、氣候變化、種族和「多樣性」等。而那些從事不那麼受左派青睞的項目的人通常只能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獨力進行。
自然而然,大學管理者就會青睞那些贏得聯邦撥款的教師。我的上一任院長告訴我,如果我想繼續建國時期的歷史研究,選題最好從「環境」角度出發。這樣,我就能有很大機會獲得聯邦撥款。
當然,我果斷拒絕了。然而很多學者都會抵擋不住金錢的誘惑,而選擇放棄原則。我猜他們可能會把開國元勛描繪成現代環保主義者,或者更有可能是環保強姦犯。
下一篇系列文章將探討:大學模式造成不良後果。
作者簡介:
羅伯特·納特森(Robert G. Natelson)是位於丹佛的科羅拉多獨立研究所(Colorado’s Independence Institute)憲法法理學高級研究員,知名憲法歷史學家,曾任憲法學教授。他著有《原始憲法:憲法的實際內容和含義》(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What It Actually Said and Meant,第3版,2015)一書。他還是總部位於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組織編寫的《美國憲法傳統指南》(Heritage Guide to the Constitution, 2014)的撰稿人之一。
原文:What’s Wrong With the Universities, and How to Fix It: Part 1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