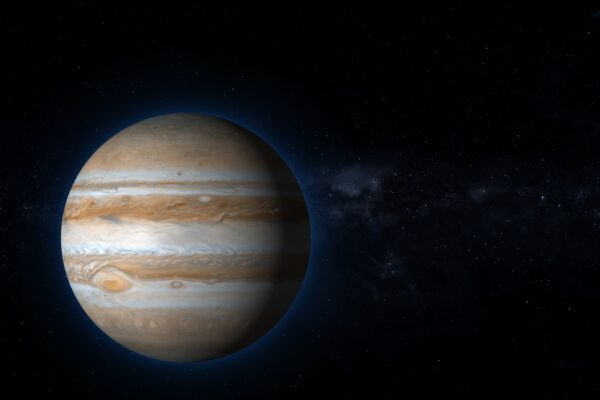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2024年02月28日訊】韋君宜,祖籍湖北,1917年生於北京,父親曾留學日本。她從小聰慧過人,後成為清華大學的高才生。她的父親斷定她是棟梁之材,想送她到美國深造。她卻毅然拋棄這一切,投奔中共。
1936年,她18歲時,加入中共;1986年,她68歲,從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的位置上退休。在追隨中共的50年裡,她經歷了許多刻骨銘心、痛徹心扉的人和事。
1986年4月,她因腦溢血偏癱;1987年,右臂摔傷骨折;1989年,再患腦血栓;1991年,骨盆又震裂。就在這接二連三、難以承受的病痛打擊和折磨下,在右手神經已經壞死的情況下,她以超常的意志,練習寫字、走路、寫作。最後,在病床上,用左手,寫完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思痛錄》。
有人將她的《思痛錄》歸納為十九痛:
一痛民族危亡;二痛失去初愛;三痛「搶救運動」;四痛失長女;五痛「鎮壓反革命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六痛「肅清反革命運動」;七痛「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八痛反右派運動;九痛大躍進運動;十痛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十一痛「反擊『利用小說反黨』運動」;十二痛文化大革命運動;十三痛挨整的同事朋友;十四痛挨整的清華校友;十五痛挨整的「一二·九運動」戰友;十六痛挨整、整人的清華老學長蔣南翔;十七痛整人、挨整的「文藝沙王」周揚;十八痛丈夫楊述;十九痛自己。
當初,像許多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韋君宜把自己對理想人生的追求,全部融注在她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之中。
她原以為,她信奉的共產主義「理想國」裡,有正義,有道德,有人性,有自由,有民主,有平等,有法治,有人權。但是,追隨中共50年,她所親歷的,與她曾經信奉的,完全相反。從延安到北京,殘酷無情的現實,一次又一次把她的理想擊得粉碎。
對「搶救運動」的痛思
《思痛錄》第一章就是回憶1942年中共搞的延安整風運動。其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澤東發動的「搶救運動」。
當時,中共懷疑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人,都是特務。1943年至1944年,特務越抓越多,從知識分子、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10歲的,一直到揪出6歲的小特務。
在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遠近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裡,整夜傳出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慘叫聲。
一位負責「抓特務」的老紅軍公開講:「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
韋君宜的丈夫,變賣家產,帶著一家老小七、八口人投奔中共的楊述,就是這樣被「逼」成「國民黨特務」的。楊述向毛澤東上書說:「毛主席,我不是特務,請你派人徹查。」然而,泥牛入海。
韋君宜也曾上書毛澤東,同樣沒有回答。於是,她絕望了,自己跑去整風班「勸說」楊述:「形勢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吧。」說完就大哭,楊述也放聲痛哭,說:「好的。」
來自四川的中共地下黨員,全部被打成「特務」,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被逼自殺。魯迅藝術學院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殺。那人叫石泊夫,是名畫家,上世紀30年代和周揚一起在上海是左翼作家聯盟的戰友。石泊夫突然被人指控是國民黨奸細,他聲嘶力竭地為自己辯白,但在場的周揚沒有為他說話。於是,他被當作「國民黨特務」抓走了。
當晚,他的妻子把窯洞的門窗都堵嚴實了,然後燒起取暖的炭火盆。一夜過去,兩個孩子和她一起「長眠不醒」。
第二天領導宣布:「她這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還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見她對黨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西北公學有個學生叫施英,中共「烈士」後代,15歲就到了延安,他也「坦白」自己是特務。有關領導根本不相信,就問他:你參加的哪個特務組織?什麼時間、地點?誰介紹你參加的?他一問三不知。領導再問:「那你為什麼坦白自己是特務呢?」他說:「(黨)號召說『坦白光榮』,『坦白有功』,又給戴大紅花,又給發西紅柿、老南瓜,還給吃雞蛋掛麵,我當然願意坦白自己是特務啦。」
延安辦了份《實話報》,專門登載誣陷人的謊話。
當時還發明了一頂帽子,叫做「不自覺的特務」,把那些實在沒有「毛病」可挑的青年都歸入此類。
「搶救運動」中,延安共打了1萬5千個特務,但最後落實下來,沒有一個是真的。
韋君宜寫道:「太荒謬了!太可怕了!到這時候我已經完全懂得了這是胡鬧,是毫無常識又對共產主義毫無信心的奇怪創造。」
「革命聖地」延安,曾經是韋君宜們共同嚮往的溫暖的「家」。經歷「搶救運動」後,韋君宜寫過一首詩,其中寫道:
「家啊!你對我們就是這般模樣?……我們如今成了外人,有辱罵,有冷眼,有繩索,有監獄……夢醒來,高原的老北風,吹得熱身子冰冷,把心撕碎放在牙縫裡咬,看還知道痛不知道?……家呀,我們對得住你,你愧對了我們……」
對文化大革命的痛思
上世紀40年代,經歷中共的「搶救運動」後,韋君宜曾和丈夫楊述議論:「現在只在(陝甘寧)邊區裡邊這樣干,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以後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麼幹,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會答應的。」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韋君宜等來的,不是上下齊心協力建設「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是沒完沒了的血腥殘暴的人整人的政治運動。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當年中共在延安「搶救運動」時最壞的做法,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重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韋君宜先是被當成「黑幫」,在「黑幫群」內互相鬥;之後,像「豬狗」一樣被驅趕回原單位,接受造反派的日夜批鬥,被勒令交代罪行。她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黨反毛」,「特務」等。
整個社會是非、善惡、正邪的顛倒,許多人良知、道德、人心的泯滅,使她精神失常整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認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殺。
她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1966年夏被紅衛兵打傻。她的丈夫、對黨忠心耿耿的楊述,被打成「三家村干將」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造反派用鐵棍打得骨斷筋折,被開除黨籍,後發配到河南勞動改造。她自己被發配到湖北勞動改造。她女兒被下放到雲南農場勞動改造。一家五口天各一方長達七年。
她在《思痛錄》中回憶:「後來,我的女兒團團對我說:『以後我們什麼書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澤東選集》,別的書都是反動。』小孩子這句話更使我一通百通。原來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資產階級文化,新的是修正主義文化。我從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資修』。」
「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都沒有根了,只請用剃刀剃就是了」。
晚年的覺醒
1976年文革結束後,韋君宜跟她女兒談了她的藏在心底很久的想法。她要寫一部長篇回憶錄,從「搶救運動」開始,一直寫到文革結束。她講,歷史是不能被忘卻的,她再不把這些親身經歷的悲慘醜惡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情記錄下來,就得帶進棺材裡去了。
於是,她開始了《思痛錄》的寫作,一邊追憶,一邊反思。
其中有一章叫《編輯的懺悔》。她說,1949年中共當政後,她「解放了」,可實際進入了一個囚籠,讓她幹的事都是欺騙讀者、欺騙工農兵。
有一篇小說,在她看來還算可以,可軍代表說,這篇作品怎麼沒有階級鬥爭?她只好和作者商量,你能不能寫點階級鬥爭?鬥爭什麼呢?就設想能不能表現階級敵人反對使用拖拉機,破壞生產。那作者說我不知道拖拉機會出什麼問題?她就帶著作者,請教懂拖拉機的人,「階級敵人」如何才能讓拖拉機出毛病、搞壞它。
1980年,她寫了一篇懷念丈夫楊述的文章《當代人的悲劇》。她寫道:「我要寫的不是我個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寫的是一個人。」這個人在十年文革中受了苦,挨了打,這還算是大家共同的經歷,而且他的經歷比較起來還不能算最苦的。「他最感到痛苦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對黨和馬列主義、對領袖的信仰,當作耍猴兒的戲具,一再耍弄。
這種殘酷的遊戲,終於逼使他對自己這「宗教式的信仰」發生了疑問。這疑問,是「付了心靈中最苦痛的代價」換來的。
她在《思痛錄》裡寫道:
「這是一部用血淚凝成的歷史……只希望這種悲劇在中國不再發生。」
「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經歷的歷次運動給我們的黨、國家造成難以挽回的災難。同時,在『左』的思想的影響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
「參加革命之後,竟使我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使我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我悲痛失望,同時下決心不這樣干,情願同罪,斷不賣友。」
「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於『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是不夠。」
「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著最高的希望······何必膽怯?我將歡迎能下決心的拙笨的民主!」
結語
韋君宜的女兒楊團追憶母親寫《思痛錄》時寫道:「母親苦苦追求了一輩子,卻在眼淚都已乾涸的時候才大徹大悟:窮盡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奮鬥,換來的究竟是什麼?當她重溫年青時的理想,當她不能不承認後來犧牲一切所追隨的,都與自己那時的理想相悖,彷彿繞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徹骨髓呢?」
為什麼韋君宜年輕時懷揣的共產主義的美麗理想,最後都變成了「革命吞噬它的兒女」的人間悲劇?
作為中共體制內的一名作家,韋君宜晚年的痛思是難能可貴的。但是,韋君宜仍然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
2004年,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通過追根溯源,最後得出結論:中共是一個以「假、惡、斗、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為本質特徵的邪教。
這才是韋君宜、楊述,以及無數曾追隨中共卻被中共的血與火無情吞噬的人生悲劇的根源之所在。
大紀元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