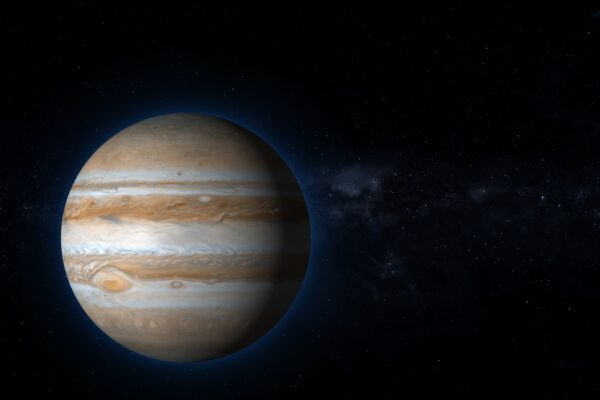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2024年04月22日訊】前 言
彈丸之地的台灣,新聞炒作的熱度無與倫比,雖說品質有待商榷,但卻可以提供一般民眾茶餘飯後的消遣,也可增進大家的知識,更能讓民眾在獲取資訊之後得以作進一步思考。尤其在政治解嚴後,新聞報導尺度的開放更提供了政府運作的種種資訊,由之可評定施政是否符合人民的福祉。
一九九二年熱鬧非凡的十八標工程弊案、基本工資調升案件,以及土地增值稅擬改為按實際交易價格徵收等等事件,在熱烈報導和討論之餘,卻在民間普遍升起一股反感之氣。姑不談事件的始末及決策品質的粗糙,由其所顯示的官商勾結、貪污舞弊,以及金權、特權的橫行,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些公共政策的擬定及施行,其實是未見其利倒先見其弊。於是我們也不得不興起「政府是否能為人民謀福祉?」的疑惑,而想藉政府力量來匡正市場失靈的主張也啟人疑竇,此時也不由得不令人想起鄭重強調「政府失靈」的布坎南教授,也更能領略為何一九八六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會落在他的頭上。這樣的思考也使我們更急切想去了解布坎南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為何他能體會出政府失靈,並奠定「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理論。我們先由布坎南的生平追蹤起。
布坎南的生平
布坎南教授於一九一九年在美國田納西州的Murfreesboro出生,祖父是田納西州州長,是一位民粹主義者(populist)。在耳濡目染的薰陶下,早年的布坎南是位「自由派的社會主義者」(libertarian socialist),直到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時才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布坎南的基礎教育是在田納西州的故鄉完成的,大學就讀於中部田納西州立大學,一九四0年畢業後進到田納西大學,一年後得到碩士學位,之後曾於哥倫比亞大學讀了一年統計學,而後進入海軍服役,一九四五年退役後捨哥大轉赴芝加哥大學。就在那裡,布坎南跟隨奈特,當選修其價格理論課程時,很快地促使布坎南由「自由派的社會主義者」轉為「市場的狂熱擁護者」。也就在芝加哥大學的哈伯圖書館(Harper Library),當布坎南正通過德語測驗之際,偶然地發現塵封在該館書架上的威克塞(Knut Wicksell)之德文著作,從此就被深深吸引而潛心研讀,對於其後的學術生涯產生無比的影響。奈特和威克塞可說是布坎南的啟蒙師,奈特本人親自為其意理架構奠基,而威克塞則是以遺作來填充布坎南學術著作的特殊觀點。
一九四八年,布坎南取得芝大博士學位,隨即返回母校田納西大學作短暫停留(一九四八~五一年),之後轉到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任教(一九五一~五六年),而在一九五五~五六年,布坎南曾獲傅爾布萊德獎金到義大利作一年研究,這也對其往後的學術工作產生頗深的影響。隨後就前往維吉尼亞大學,而他的學術生涯也就離不開維吉尼亞州,他在該州的三所大學待過。一九五七~六九年,在維吉尼亞大學共教了十二年,一九六三年還與都洛克(G.Tullock)在該校共同創立「公共選擇學會」(The Public Choice Society)。他也與納特(W. Nutter)在維吉尼亞大學共創「傑佛遜政治經濟中心」(The Thomas Jefferson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該中心一九五八~六九年的主任就是布坎南。一九六九~八三年,布坎南又轉赴維吉尼亞工學院當「大學傑出講座教授」(The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他在那裡又與郭斯(C. Goetz)和都洛克共創「公共選擇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一九八三年,該中心移至喬治梅遜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布坎南也隨著轉到該校繼續擔任中心主任,同時擁有「哈里斯講座教授」(Holbert L. Harris University Professor)頭銜。
除了得到芝大博士學位外,布坎南也分別在一九八二和一九八四年獲得Giessen大學和瑞士蘇黎世大學的榮譽博士。他也同時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EA)的兼任學者和「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自一九七六年起)。一九八三年,布坎南就一直是「美國經濟學會」的傑出會員;一九六三年曾擔任「南方經濟學會」(The Southern Economic Association)會長,一九八三~八四年也當過「西方經濟學會」會長;一九八四~八六年又曾擔任很特殊的「蒙貝勒蘭學會」會長;一九七一年亦曾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一九八四年獲得政治經濟Frank Seidman傑出獎;布坎南也擔任「合理基金」、「孟格研究所」、「胡佛研究所」、以及邁阿密大學「法律和經濟學中心」的顧問。當然,一九八六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布坎南成就的最高峰,而其得獎雖受許多人讚賞,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意外,且引起了相當的爭議。因其著作鍼砭政府活動規模的大小和範圍,一位報紙專欄作家還曾認為其著作比較像是政治性的專欄,而不太像是學院人士的作品。
布坎南已婚,但膝下無子女,他被其某些同事形容為嚴峻而冷酷。他們說他威逼學生的樣子好似要證明他是學術先鋒人物似的;也有人說他精力過剩,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激勵他作批判性思考,並且提升表現水平。布坎南自認是經濟學界的「非主流」,而且有時會有寂寞、孤獨的感覺。三十年來,布坎南一直想將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看法與街頭市民溝通,但往往有著打敗仗的沮喪感。
既然布坎南對主流經濟學有格格不入之感,而他的榮獲諾貝爾獎也引起爭議,到底他的理論是什麼?他的學術貢獻又是如何呢?
布坎南的學術貢獻
布坎南的研究領域在福利理論,他自認其主要貢獻在整合政治決策分析(公共選擇)於經濟理論體系,這也就是所謂的「公共部門經濟學」。他將經濟分析延伸至應用於體制的選擇,基於政治決策結構分析來批判凱因斯總體經濟政策、澄清機會成本理論,並且批判後凱因斯學派的公債理論。
瑞典王家學院之所以頒贈諾貝爾經濟學獎給布坎南,也就是表彰他在公共選擇學說領域及延伸該理論的貢獻。布坎南將經濟學和政治學巧妙地結合,利用經濟學家分析私部門的傳統基本經濟公理—個人決策者追求私利,來解說公部門理論。不過,私部門中個人的自利行為是在增加更多的商品,但官僚體系中的政客們的自利行為,卻產生對社會有害的結果。因此,為了改進政府的功能,布坎南進一步發展出一套組織理論,強調法則在制定經濟政策時的重要性。
布坎南總共在學術期刊和書中發表了約三五0篇文章,他的重要文章蒐集在《經濟學家應該做些什麼?》(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及《自由、市場和國家》(Liberty, Market and State)兩本書中,他還寫作了二十本書。布坎南的最重要著作是與都洛克合作的《同意的計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1962),早年他曾寫作《公債的公開原則》(Public Principles of Public Debt, 1958)和《財政理論和政治經濟體系》(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1960)兩本書;接著他又寫作及編撰了較有名的書有《民主制度下的財政》(Public Finance in Democratic Process, 1966)、《共有財的需求與供給》(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 1968)、《成本和選擇》(Cost and Choice, 1969),《自由的極限》(The Limits of Liberty, 1975)、《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 1978)、《制度性契約中的自由:一位政治經濟學家的期望》(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Perspectives of a Political Economist, 1978)、《租稅力量》(The Power to Tax, 1980)、《競租社會的理論》(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1980),以及《規則的理由以及赤字》(The Reason of Rules, and Deficits, 1985)等等。除了這些書外,布坎南發表在著名學術期刊上的文章也有近一七0篇,另外幫別人的著作寫序及評論文章也多得不勝枚舉。
布坎南堅持以「個人」作為任何分析的基礎,這也成為他的著作之標記。在經典之作《同意的計算》中,他與都洛克以理性的、充分認知的、效用極大的個人行為作基礎,推導出一套集體選擇的理論,該理論有四點有趣的引申:其一,法治的需求是理性的;其二,簡單的多數決只不過是眾多可能規則中的一種,對於個人而言,這個規則卻可能不是最佳的;其三,不同的政府活動可能採取不同的決策規則;其四,支持公部門活動而不贊同私部門行為,取決於是否存在有能夠反應出集體行為的預期成本低於個體行為的成本之投票規則。該書成為對重新審視基本政治的和政府的決策過程和規則的一項呼籲。
在《赤字中的民主》一書中,布坎南和華格納(R.E. Wagner)提供了如何應用公共選擇理論的實例。他們認為,在凱因斯學派當道之前,公私部門財源相互類似這種觀念廣為週知,由而公部門支出來自稅收的觀念也被認為理所當然,於是便對政府支出形成一種有效的限制。不幸的是,這種道德限制卻被凱因斯學派的主張粉碎,政府財政赤字也就從此長期間的出現。在該書中,布坎南指責凱因斯學派經濟學放縱政客們,將政客們的限制摧毀,在凱因斯學派靈丹的保護下,政客們不必受租稅的約束而一再的膨脹支出。為了彌補這種缺口,有必要對超額預算作限制而保持預算平衡,唯一的辦法只有經由變動憲法架構,於是需要一種更嚴格的投票規則,如此也才能達到財政責任和維持長期的經濟安定。為了支持這個理論,布坎南和都洛克在一九七七年合寫一篇實證文章,以資料證實公部門在失控下,公務人員薪水相對於非政府部門人員薪水的提升,只能由官僚的政治力來解釋,而官僚則以施加壓力來合乎他們的自利。布坎南也曾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公部門成長為文提出警告,他一再的呼籲制定抑制政府膨脹的法則。
在一九八0年,布坎南和拓利遜(R.D. Tollison)及都洛克在《競租社會的理論》這本書中,提出另一種政府支出浮濫的源頭,這就是當今甚為熱門的「競租」(或鑽營,rent-seeking)行為。此即利益團體為了得到政府賦與的獨佔、關稅,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特權,利用遊說、利誘、賄賂等等方法來得到,而這些活動是將資源浪擲在遊說政府官員上,使生產性活動的資源短少。
在宣布榮獲諾貝爾獎之後,布坎南在一篇演說詞裡強調,一般國民已體認到,必須變動規則來抑制政府的角色,他認為當時雷根的連任是一大佐證。布坎南提供的改變政治遊戲規則的藥方,已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布坎南曾抵台參加蒙貝勒蘭學會在台北召開的特別會議,並在會中發表了「工作倫理的簡單經濟學」(Simple Economics of the Work Ethic)專題演講,他由自己觀賞橄欖球賽的經驗談起。由於四場球賽須耗十二個小時,雖然轉播時間在週末休閒日,而布坎南也喜好看球賽,但心理有「虛度光陰」和「罪惡感」。為了消除該種感覺,在觀賞球賽的同時,布坎南一面做著「敲核桃」的工作,如此即可補償看電視這種「浪費時間」的損失。布坎南以清教徒傳統的「工作倫理」來解釋這種體驗,他也認為台灣的傲人經濟成長經驗,就是與工作倫理有密切相關;他同時認為美國經濟的走下坡,也與其新生代丟失清教徒的工作倫理傳統有關。
布坎南得獎的迴響
上文提過,布坎南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引發一些非議,一位報紙的專欄作家認為布坎南的著作倒像是政治專欄作家的產品,而不太像是學院人士的作品。多位學術界人士也對布坎南的著作提出質疑,例如,D.E. Moggridge在評論《赤字中的民主》一書時,對於布坎南的兩種立憲補救辦法——平衡聯邦預算和要求聯邦準備銀行維持一個貨幣法則,認為以選擇理論的使用,會使投票者或政客,願意選擇憲法限制的說法,Moggridge覺得並不能說服人;即使是另一位保守的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勒也批評公共選擇學派無法以實證來支持他們的理論。同樣地,Zeckhauser也對競租導致浪費資源的說法,要求布坎南等人提出實證。
儘管有這些批評和要求,卻並沒能否定布坎南的理念,只是要求布坎南再精益求精。而經過布坎南這一群人的努力後,如今在公共選擇領域上已有許多忠心跟隨者,而且在各個層面上都有進展。最值得一提的,在市場失靈是否能由不完美的政府來醫治、政客和官僚是否有生產力動機方面,已受到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政府的「診療」是否反會帶來禍害?政治學家們已愈來愈多人利用公共選擇理論解說政府官員的行為,而當今全球風行的自由化、反管制運動與平衡預算的要求,也至少有部分應算入布坎南的貢獻。
在布坎南得諾貝爾獎時,一定有不少人為都洛克沒有共同獲獎而困惑,甚或不平。因為布坎南的公共選擇學說脫離不了都洛克的影子,連布坎南都承認在奈特和威克塞之外,都洛克是第三位對他影響最大的人物,且也認為他的公共選擇理論之奠定,是受到都洛克的啟發和協助。我想這個疑問只有瑞典王家科學院的有關人士能夠解答。
布坎南的研究也就是俗稱的「政治經濟學」,而古典經濟學家原本就是在做這件事,布坎南可說做了「復古」工作。不但將一九三0年代之後風行的凱因斯理論做了嚴厲批判,重新對政府的行為作深層檢討,布坎南同時也將經濟理論重新帶回人間。他在李甫基這位法國記者所著的《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Tomorrow, Capitalism, 1982)一書的序言中說:「我們現在的經濟學家,在專門的學術刊物上寫作或對談,只是學術圈內的事,很少或根本完全沒有向社會大眾表達出什麼。對於經濟政策的實際問題,在平日都由一些非經濟學家提供證據。對於這個事實,我們難道不覺得驚訝嗎?……古典經濟學家都是社會改革家,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自己的觀念對於個人幸福,以及對國家財富所作的貢獻。他們也把這些觀念所引發的內在力量傳達給社會大眾和民意代表。……在現代經濟學家的著作中,除少數例外,竟沒有表現出一點意識形態上會令人興奮的精神。……現代經濟學,大都沒有焦點、目標。」
布坎南對於政府失靈和經濟學家、經濟學的批評,同樣能給台灣社會帶來反省;尤其當六年國建計畫所曾產生的風風雨雨,買票猖獗的選舉制度所暴露的金權政治當道,社會福利措施的陸續推展,以及國人缺乏正確的經濟觀念之今日,更顯出布坎南的學理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性。
註:本文由原載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經濟前瞻》第七卷第四期同名文章修改而成。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