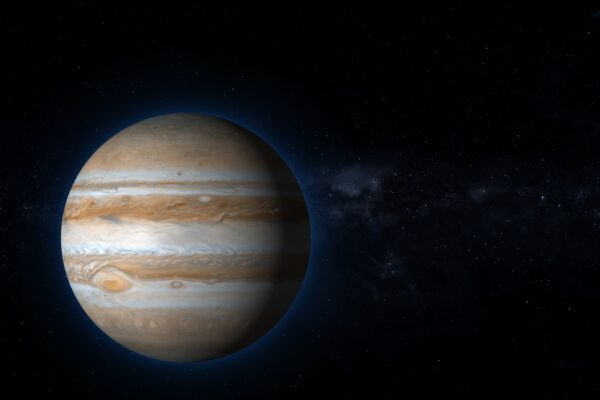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2025年12月08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Dustin Bass撰文/柳嵊濤編譯)槍聲在酒館內驟然響起。一名男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赤手空拳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站在那個痞子面前,體會著這一刻——這一刻將鞏固他在惡地(Bad Lands)蠻荒世界中的地位。
在倒地前痞子於酒館中不停挑釁過往客人,還朝店裡的時鐘開槍。當羅斯福進入時,他朝羅斯福大喊:「四眼仔!四眼仔要請客!」羅斯福只是笑了笑,便走到一旁桌邊坐下。挑釁者雙槍上膛,大步走向羅斯福,俯身逼其買酒。羅斯福假裝順從地站起身,隨即快速給了對方頭部三記重拳。
「他倒下時頭撞到了吧檯的角」,羅斯福回憶道,「我把他的槍拿走,屋裡其他人這時也開始紛紛譴責他,把他趕出酒吧並塞進棚屋裡。」
那是1884年夏天。羅斯福回到惡地荒原,打算成為一名「牧場主」。他剛剛給了馬耳他十字牧場(Maltese Cross Ranch)的主人一張14,000美元的支票,用於購買450頭牛,並計劃開辦自己的牧場。羅斯福此行目的並非源自財富與機遇。悲痛驅使他從曼哈頓的喧囂街道逃至荒地那片「憂鬱而無徑可循的平原。」
被悲傷驅使

羅斯福在此前剛剛度過其人生中最嚴酷的一個冬天。1884年2月14日,他在日記中重重劃下一個大大的「X」,並寫下:「我生命中的光已熄滅。」
那一天,羅斯福的妻子愛麗絲(Alice)與母親米蒂(Mittie)相繼去世——距愛麗絲生下他們的女兒僅僅兩天。他對這一雙重喪親的反應,便是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這與六年前父親去世時他的反應如出一轍。然而,即使用高強度工作來麻痹自己,悲痛依舊在侵蝕著他。
「他越發感到那種可怕的孤獨」,他的妹妹科琳(Corinne)回憶道。「我擔心他睡太少,因他常在夜裡走來走去,且眼睛紅腫而疲憊。」

為擺脫對妻子和母親的種種世間回憶,羅斯福決心出售自己的房子,連帶父親在1873年購買的家族宅邸。羅斯福一家需在5月前徹底搬離。5月下旬,羅斯福作為紐約州的全權代表抵達芝加哥,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發表支持其厭惡的候選人詹姆斯‧G‧布萊恩(James G. Blain)的聲明後,羅斯福從政壇隱退,並繼續西行。他將年幼的女兒託付給姐姐巴米(Bamie)照顧。
羅斯福視前一年短暫到訪過的惡地荒原不僅僅為環境的轉變,更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世界。在這裡,「文明彷彿遙不可及,就像我們生活在久遠的過去。」在這片荒野中,羅斯福將進行狩獵、騎馬、驅趕牛群,閱讀書籍,並全身心地投入寫作。

這位哈佛畢業生、前政治家對荒原的孤寂帶有一種獨特欣賞。幫其建設埃爾克霍恩牧場(Elkhorn Ranch)的好友比爾‧蘇厄爾(Bill Sewall),對羅斯福關於這片土地的看法感到困惑,甚至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要麼對生活有扭曲的理解,要麼自我厭惡,或者兩者兼有」。或許蘇厄爾說得沒錯——羅斯福此時的生命之光已滅。過去幾個月間他在紐約的種種行為、在平原上無休止的遊蕩,以及最近的酒館打鬥,都表明他並不畏懼死亡。但這些同時也顯示,他在努力尋回那束曾經的光。
超越悲痛

羅斯福常騎著他那匹「步伐極穩」的坐騎馬尼圖(Manito),從黃昏一直馳騁到黎明。他在這種自由中體驗到了無窮活力——這種自由,除了那些自願在荒野中生活的人外,很少能有人體會。他的馬「和密蘇里河流域上的其它馬一樣快」,讓他得以超越悲痛。他寫道:「疾馳的馬背上,憂愁很少停留。」
到了8月,羅斯福、蘇厄爾和威爾莫特‧道(Wilmot Dow)建立了埃爾克霍恩牧場,不過牧場房屋的建設要到10月才開始。儘管如此,對於一個希望能與自己思緒獨處的人來說,這個位置再理想不過。他最近的鄰居至少相隔10到15英里,馬耳他十字牧場也有約40英里的距離。在一個人時,羅斯福從未閒著,他經常會在自己視作「理想的英雄之地」上穿行。

就在埃爾克霍恩牧場建立的同一個月,羅斯福與另兩人出發前往比格霍恩山脈(Bighorn Mountain),並整整離開兩個月。他騎著馬尼圖,攜帶刻有鹿、美洲野牛和羚羊定製圖案的槓桿式槍機操作的45-75溫徹斯特步槍(Winchester Rifle)。他似乎毫不受大自然對他和同行者們嚴酷考驗的影響。
他寫信給姐姐巴米說:「有一天,我們在傾盆大雨中騎行,後來大雨演變成冰雹和狂風暴雨,近乎掀翻馬車,還把小馬們嚇得不輕。我們最終躲進了一處溝壑。還有一次深夜,一陣暴雨襲來,而我們正在露天外躺著(我們沒帶帳篷),最後只得裹在濕透的毯子下打顫到天亮。」
在這次漫長探險中,他獵殺了數百隻鳥類和小型獵物,還射殺了黑尾鹿、馬鹿以及一頭1,200磅重的灰熊。
惡地的孤寂與嚴酷環境,漸漸開始治癒羅斯福,並為其提供了在紐約乃至剛到平原時都無法得到的東西。

「我玩得很盡興」,他在9月20日給巴米的信中提到,「也經歷了足夠的刺激和疲憊,以至於不會陷入過多地沉思;且我終於能在夜裡安穩地入睡了。」
務實的關注
在大衛‧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著作《馬背上的清晨》(Mornings on Horseback)中,他指出:「羅斯福在惡地荒原得到的最直接且重要的益處,便是他的身心確實得到了恢復。」
羅斯福在荒原的時光自1883延續至1886年,儘管在此期間他時常回到紐約。牧牛、狩獵和在平原馳騁占據了他大部分時間,但即便經過漫長的一天,他仍會抽出時間進行閱讀和寫作。

1885年,他出版了《牧場主狩獵行記》(Hunting Trips of a Ranchman),詳細記錄了自己在荒原的冒險經歷。他對這些地方的未來有著清醒的認識。好似羅斯福當時的人生階段,其評述中帶有一絲哀傷的色彩:「牧場主得以享用戶外的自由,是這個國家最愉快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於其本質,這種生活註定會非常短暫。」
「廣袤無垠的草原已被劃定,很快將分割為若干狹小地塊。若說近幾年白人定居潮像洪水般席捲西部,也並非過於誇張;而牧牛人只是浪尖上的水花,雖被拋得很遠,但很快便會被淹沒。」
美國正逐漸成為工業強國,而這種轉變也進而影響了環境的變遷。羅斯福擔心,有著成片美麗景色的土地很快會被商業化。此外,他還擔心大片林地會落入富人手中,而普通美國人將被排斥在外。
在其1893年出版的《荒野獵人》(The Wilderness Hunter)中他寫道:「從本質上說,獵人的生活方式在多數地方都會是短暫的;而一旦這種生活消逝後,在那些歷史悠久的定居國度裡,便再也找不到真正的替代。」
「在私人獵場射獵,不過是令人遺憾的滑稽模仿;在環境改變後,這項運動中最具陽剛氣概與健康的特質便消失了。因此,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我們需要一套嚴格的動物保護法,並嚴格執行。同時不僅是允許,更得說是必要,建立由國家管理的大型森林保護區,這些保護區也應作為野生動物的繁殖和棲息地;否則我將非常遺憾地看到,這個國家將逐漸湧出一片大型私人獵場,僅供極富有的人享樂。荒野生活的一大吸引力來自其粗獷而質樸的公正性;在那裡,每個人都將得以展示自己最真實的一面。」

保護荒野
羅斯福當然是位富有的人,這進而使他的上述發言更具說服力。他正是那種「粗獷而質樸的公正性」治癒下的產物。在荒野歲月結束時,羅斯福的身心確實得到了恢復。曾經熄滅的生命之光被重新點亮。他準備重返政壇,但更重要的是,他已準備好再次去愛。1886 年12月2日,他與兒時的青梅竹馬伊迪絲‧卡羅(Edith Carow)再婚。羅斯福希望所有美國人都有機會像他一樣接觸和感受荒野。
1901年,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遇刺後,42歲的羅斯福就任,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同時也迎來了踐行這一理想的機會。羅斯福通過推廣土地保護區進行保護工作。在任職總統期間,他建立了美國首批18個國家紀念園區、5個國家公園、55個聯邦獵場和鳥類保護區、150個國家森林,以及約2.3億英畝的公共土地。他還成立了美國林業局和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系統。羅斯福因此被稱為「自然保護總統。」
在為《荒野獵人》撰寫序言時,羅斯福試圖傳達其親身經歷所產生的重要意義。他列舉了所有來自荒野的治癒力量——並希望這些治癒力量能繼續惠及未來的美國人。
「除非親身經歷過,否則無人能體會在孤寂荒原中狩獵的極致樂趣。對於親身經歷的人而言,那樂趣在於駕馭駿馬,穩握獵槍;在於終日的辛勞與堅韌,最終以勝利加冕。多年以後,他的腦海中將永遠浮現那無盡草原在明媚陽光下閃爍的景象;那灰色天空下白雪覆蓋的荒原;那令人憂鬱的沼澤;滔滔奔湧的河流;夏日常綠森林的清新氣息;冬日冷風拂過松林的低吟;瀑布在蒼茫山巒間咆哮;無數的景象與聲響;浩瀚與神祕;以及那靜謐深處潛藏的寂靜。」
原文:Theodore Roosevelt, the Bad Lands, and Healing Power of the Wilderness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