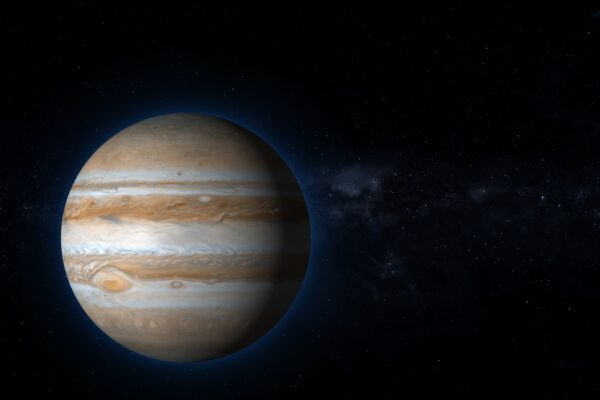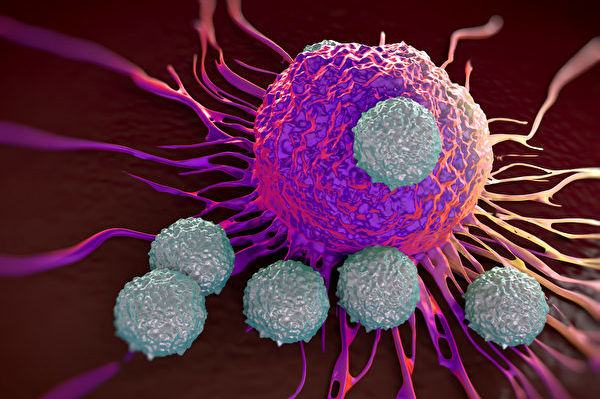【大紀元2023年10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圓明採訪報導)「我的啟蒙是非常晚的。基本上我的人生最寶貴的年華,都做了五毛和粉紅……」白流蘇是一名退役女兵,從一個極端的小粉紅到認清中共的謊言與殘暴,她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白流蘇來自中國深圳。深圳戶口可以辦理一年多次(「一週一行」)香港簽注,白流蘇經常去香港,感覺香港跟大陸完全不一樣。「我們家柴米油鹽很多都是在香港買的,包括我小孩打的防疫針。」
「我對香港的制度是很嚮往的。中共它是一個獨裁的政黨,很多的社會資源是被它剝奪的,對宗教信仰打壓很嚴重。香港是我們中國人僅剩的一塊文明土地了。」她說。
十年前的白流蘇可不是這樣。她曾在部隊服役,非常極端地熱愛中共政權。
入伍
2005年,白流蘇高中畢業時,家裡人為給她找個出路,想著部隊復原了,可以分配個正式的工作。徵兵的時候,家裡就花了很多錢讓她去部隊。
白流蘇說,女兵是有名額的,在兵總部名額就被各種關係瓜分了。要找到有這種資源的人,不能轉帳,要給現金,然後拿到一個名額,去體檢。「我們當時花了二十多萬。新兵連的時候,班長讓我們坐在地上一個個問,報數:你家花多少錢?他花多少錢?大家都心知肚明。」
白流蘇被分到北京某通信部隊,是全軍通訊的龍頭老大,待遇非常好,看病是在301醫院,吃飯伙食也不錯。長話站是保證一號台的,專門轉接一號人物的電話,保密性強,那些領導人的電話號碼每週都會換。
進去部隊後,白流蘇才發現這個地方特別腐敗。
「新兵來了都是挨打的,班長還讓我們都脫光,就那麼變態。還問我們要錢,我們都要給他錢。長話站那些女兵,還被領導拉去陪酒。京西賓館同年兵提幹的兩個人,大家都說她倆是陪睡陪出來的,喝酒喝出來的,特別不堪。」
一號台每年有兩個提幹名額,不但要業務好,家庭背景好,政審要過關。要麼關係特別硬,要麼放得開,才能提幹。白流蘇打定主意混兩年就回去找工作。她不想提幹,更不想付出那麼多去提幹。
她發現部隊臃腫不堪,還有很多機器、設備天天擦得倍兒亮,但沒有用過。因為機器保養壞了屬於自然損耗,用壞了就要承擔責任。「部隊那個體制,我覺得打仗是不可能的。」她說。

一年後,父親託人找了副團長,就讓她去學習護理員,調離了長話站。
有一次,她給一個山西的受傷男兵換藥。這名男兵的股骨頭壞死了,悄悄告訴她是在新兵連被打的。白流蘇哭了,心想年輕人這一輩子怎麼辦?很快有人告發了她,軍醫就不讓她再去給這個男兵換藥了。
「在部隊是不能一個人走路的,一定要兩個人或者三個人才可以,互相監督。幾個人一個房間,而且欺負新兵,讓我一個人打掃一層樓的房間。」原本一心保家衛國的白流蘇沒想到部隊這麼爛,「欺負新兵到什麼地步?就讓人在那打。那些男兵挨打得更厲害,訓練中班長看誰不順眼,一腳跺到肚子上,踢多遠,都到那種地步。」
白流蘇慢慢明白了,這就是一種訓練。在社會上相對自由,人們可以稍微反抗,有一些自由的意識。進入部隊之後,它首先要把這種反抗精神磨滅掉,讓你完全順服它。
「讓你做內務,把被子擀一擀、疊一疊,疊得倍兒正,如果疊不正的話,就各種體罰你,讓你沒有獨立思考的空間,就徹底地洗腦你,馴化你。」白流蘇回憶,疊被子把手都磨出泡了。
一個山東的老班長就對她說,你有沒有聽說過馴鷹技?老鷹剛抓回來是特別鋒利的,反抗要叨人的,放鷹人就不讓它睡覺,不讓它吃飯,把它的鬥志都磨滅掉,它才能聽它的主人的話。
「我印象特別深。我說天啊,原來疊被子就是為了訓練我們啊,它就磨滅你的鬥志,訓練你,把你訓練成國家機器。」
粉紅
白流蘇說,它洗腦確實很成功。「我們就對那些所謂的外來勢力,美國、加拿大,包括台灣,都義憤填膺了。那時候陳水扁要競選總統,如果他一旦上台要全民公投(加入聯合國),那一年我們在做戰前動員會。
「中共前國防部長梁光烈在我們團的山洞裡住了快兩個月,那時候梁還是總參謀長。就準備如果陳水扁一上台全民公投,這邊就開始打仗了,整體都在做戰備。
「我們整天在部隊學習,搬個小板凳去會議室看新聞聯播,每個禮拜都要去學習反心戰,反滲透,還反間諜。我就不理解,我說咱這有啥?就鍋碗瓢盆的,有間諜嗎?」
有一次,在大禮堂放紀錄片。內容是團裡有個通訊大學畢業的小伙子,做技術的軍官。他在部隊得不到重用,也不讓他轉業,他就走了,在外邊接活做IT,就被判刑了。指導員說他背叛祖國、背叛軍隊、背叛人民,所以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這個體制很可惡,特別可惡。」白流蘇認為,中共的這種所謂的思想教育,其實是從小開始的,只要是在大陸長大的,從小到大被共產黨洗腦。只不過是部隊裡就完全變成真空罐了,外面的信息是潑不進來的。
「我從小就是喝著毒奶長大的,那我肯定就變成戰狼了。」她說,「它就奴化你,讓你定點吃飯,定點睡覺,定點訓練,所有的事情以長官為主,一吹哨你就要去。最後變成什麼樣呢?你就按照它的培養,讓你打仗,你就熱血沸騰地去打仗了。它給你灌輸你就是國家的機器,你是沒有個體的。」
覺醒
2007年,白流蘇退役了,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工作,結婚,生子。先生是個書讀多了就有思考的人,二人有了孩子後,先生希望她把小孩生在美國。這成為白流蘇思想啟蒙的源起。
「一開始我根本就不想去,說美國有啥好的,非要把小孩生在美國,中國還盛不下你了?去美國之後住兩週,一吵架,我坐著飛機又回去了,挺個大肚子。先生不敢逼我了,天天半夜醒來唉聲嘆氣的,說『我兒子要做韭菜了,要被人欺負了』,就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白流蘇擔心丈夫生病了,孩子34週的時候,她又坐飛機從廣州飛到拉斯維加斯,開始在美國生活,生孩子。
白流蘇發現,美國跟她想像不大一樣,大街上沒有到處「嘎嘣」打槍的,去醫院人家彬彬有禮的,也沒有亂收費,人們都很友好。
待產無聊,她就在家看YouTube視頻,8964真相對她的衝擊力非常大。「我心裡非常難受。我一看到那些對學生開槍的,還有天安門母親說的話,我真的心裡特別痛苦,覺得特別屈辱,我怎麼愚昧了這麼多年?去部隊服役了幾年?我怎麼會為這麼邪惡的一個政權,像希特勒一樣的政權,為它去效勞呢?」
「還有法輪功活摘器官的內容,在國內我是不知道的。就算我去香港,人家給我塞法輪功資料,我不相信,我看到YouTube詳細介紹的視頻之後,真的是徹底把我顛覆了。我晚上睡不著覺,在那哭。」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我那時候的心情,覺得自己完全被矇騙了,很氣憤,很傷心,很絕望,但是又不知道怎麼去反抗,真的是很痛苦。」房東就開車帶她到處轉一轉,給她做飯,帶她去教會。
最終,白流蘇選擇小孩北京時間6月4號出生。本來預產期是在6月10日,但滿39週在加州就可以剖腹產,合法做手術了。
「我覺得要紀念一下。那些年輕人對於他個人來說沒什麼政治訴求,他就是盡到了一個公民的責任,希望中國去改革,希望這個國家民主、變得更好。那時候的大學生多稀缺啊,就這樣白白地犧牲自己的生命。」她說。
抗爭
在美國生完小孩後,白流蘇回到中國,她感覺一天也不能再待了,如坐針氈,她已經清晰地認知,中國是一個獨裁、威權國家,中共是個很殘暴的政權。
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爆發,她很擔心中共會開槍。但她還是想去參加遊行,8964沒趕上,這次她要聲援這種自由民主運動,香港畢竟不會像大陸那樣吧。白流蘇帶著小孩參加了中環抗議的快閃。
她回憶,當時香港學生周梓樂被黑警從停車場推下,官方對外公布說他是自殺的,大家都很氣憤,很多市民都參加遊行抗議了。「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有年輕人失蹤的。」
2019年底,白流蘇又懷孕了。居委會的人讓她去做流產。那時候中國還沒有放開三胎政策,他們面臨天價罰單,或者被單位開除。這些都是他們無法承受的。
特別是「港版國安法」通過後,令人瑟瑟發抖,國內也在一直不停地抓人。白流蘇決定逃出中國,於2020年2月到達新西蘭。不幸的是,由於長期壓力過大,腹中的小生命在三四個月的時候流產了。
2021年3月,白流蘇的姐姐因病去世。白流蘇因為在新西蘭參加一些活動,不敢回國奔喪。她特別傷心,跟姐夫商量,姐姐是佛教徒,給她買佛教徒的那種骨灰盒?姐夫說不行,她是共產黨員,得按照共產黨員的骨灰盒去給她買。
「我都覺得特別無語。這人死了都不放過嗎?我覺得黑社會的人要是死了,他家屬想選什麼樣的骨灰盒,也是自由的吧。共產黨人他就不自由了。」
希望
白流蘇表示,自己之所以能轉變,就是因為法輪功、還有「六四」這些視頻,她也經常看新唐人電視和大紀元新聞網。
「我本身不煉法輪功,我不是法輪功的成員,但是我捍衛法輪功的宗教的權利,這是最基本的人權。作為一個人他有權利選擇他的宗教信仰。」
白流蘇認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超過政治犯。任何一個獨裁國家對政治犯的打擊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在中國不是,中共是對法輪功的迫害排在第一位的。「我同學有煉法輪功的,現在都沒影兒,都沒聽說過有任何消息。」她說。
「我們做個中國人太難了。我們要求的過分嗎?我們只是要求一個作為人的尊嚴,人生下來的那一點點權利,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怎麼都這麼難?」白流蘇希望下一代不再經受同樣的苦難。
她說,「我的啟蒙是非常晚的。基本上我的人生最寶貴的年華,最青春的時間,最好的年華,都做了五毛和粉紅,占據了我所有的思維。
「我反對共產黨,完全是那種發自內心的。我覺得我身上所受的全部的苦難,都是來自於共產黨,就是這個體制帶給我的,這種獨裁威權體制。
「一個社會的文明取決於對個人權利的捍衛,個人權利得到捍衛了,這個社會才可能會文明。如果一個社會號稱它是21世紀最幸福的國家,連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國家,它還會文明嗎?不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