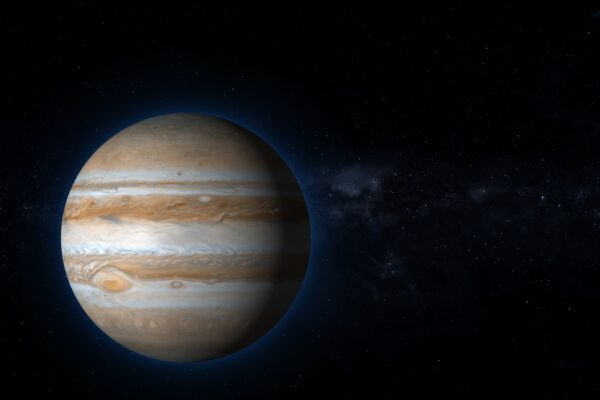翻遍多佛到迪爾海岸之間易碎的斷崖邊緣,我找到十來株珍珠色的花穗,從稀疏薄草之間抽長出來,肯特郡的熾陽把野草烤得乾枯。我蹲下來,仔細觀察列當的特徵。好的樣本要有黑色柱頭、長而蜷曲的苞片、毛茸茸的花絲,這些絕不會有錯。小一點的比較難分辨,因為特徵很大程度上與隨處可見的表親小列當重疊,而小列當在這裡也有生長。我從找到的每一株上都取了一點組織,但為了回到實驗室後的DNA檢驗,我需要更多樣本——看來躲不掉了,我必須攀到斷崖的外面去。
下午近晚,陽光依然炎熱。崖頂的草皮上,藍蝴蝶在蟋蟀此起彼落的鳴叫聲中漫無目的翩翩飛舞。奶藍色的海峽波光粼粼。一條蜿蜒的小徑在荊棘叢和草叢簇生的圍場間繞進繞出。圍場裡有馬,也有一叢叢紅籽鳶尾(Iris foetidissima),我自得其樂,摘下一片葉子揉碎,聞起來和烤牛肉如出一轍。沒多久,只見忙碌的多佛港出現在我左手邊,往海平線一直延伸出去,彷彿一座由車輛、起重機和管線構成的工業園區半沉於海裡。我探出高聳的白堊斷崖往下看,遠處,浮泛白沫的海水靜靜淘洗著山崖腳下的巨石。碎裂的白堊如一縷煙霧,慢動作沉向深海,有如在墨水裡注入乳白的雲。就在那裡,在一塊突出的石磯下方幾公尺處,就是我要找的東西:一叢象牙白色的毛蓮列當花穗,令人難以抗拒。
我不是有合格證照的攀岩專家,我不懂行話、不會繫繩、不會打結,但為了尋找植物,我一輩子都在練習攀爬。我背抵著山壁,一寸寸往下移動,掌心直冒冷汗。別往下看。一點一點地,我挨到突出的一塊岩石上,岩面只有三十公分寬,而且比我想像的還要不平穩,不過我可以坐在上面,雙腳伸出邊緣擺盪,這倒不會太難。在這魔幻的一刻,天地間只剩下我與這些特別的植物,以及頭上、腳下、身後的多佛白崖,還有在眼前無盡延伸的海峽——甚至不會有人看見我在這裡,或許這樣也好,不然要是有人看見了,肯定會聯絡救難隊出動。
像是看穿我的心思似的,某處忽然響起警鈴聲,我嚇了一跳,隨即意識到是下方的渡輪站傳來的。「請注意,以下安全宣導事項……」和緩的女聲在斷崖上來回晃蕩,聲音和演員茱蒂.丹契(Judi Dench)異常相像。魔幻被打破了,我只好開始做正事:觀察、測量、蒐集、塗鴉。我小心翼翼扭動姿勢,希望拍個一兩張照片。「若您察覺異狀……」茱蒂.丹契這時接著說。看來最好該吿辭了,免得底下渡輪站的人發現我。我抬頭環顧在我和山徑之間向上展開的垂直陡壁。才一站起來,白堊碎屑就像發出嘈雜水聲的小溪從我腳下鬆動滾落,消失在深淵之中。我抓住岩塊,掌心滲汗。這是很冒險的事。我再三安慰自己,既然能找到路線下來,爬回去肯定也不會太難吧。忽然,不知哪裡來的一隻巨大白海鷗從下方一邊尖聲怪叫,一邊盤旋向我飛來。我驚恐發現,牠想把我趕下岩壁!這隻獅鷲般的怪物彷彿自惡夢現身,繞著我兜圈子,像鎖定獵物的駭人猛禽,伸長尖利的橘爪猛撲。這是正常海鷗該有的行為嗎?「滾遠點,你這個畜生!」我大吼,身體搖晃之際,腳下踉蹌差點滑倒。我倉皇抓住一簇雜草穩住重心,然後一邊摸索能抓握的地方,一邊向上爬,一路又踢落更多紛飛的石屑。我一次謹愼跨出一步,好不容易扒緊岩石,往上一撐,總算回到峭壁頂端。海鷗放聲大笑。
這哪裡是植物學,這簡直是玩命。
我頭昏眼花,拖著腳步回到安全的地方,手掌髒兮兮地沾滿白堊土、汗水和血。海鷗似乎很滿意我不再侵犯牠的地盤,繞了兩圈飛走了。我拍掉身上的泥沙,無言地動身回民宿去,心裡吿訴自己,我再也不做這種事了。
——但我還是做了。
(網站專文)
本文摘自《牛津植物學家的野帳》,一卷文化提供
責任編輯: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