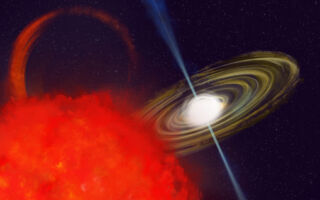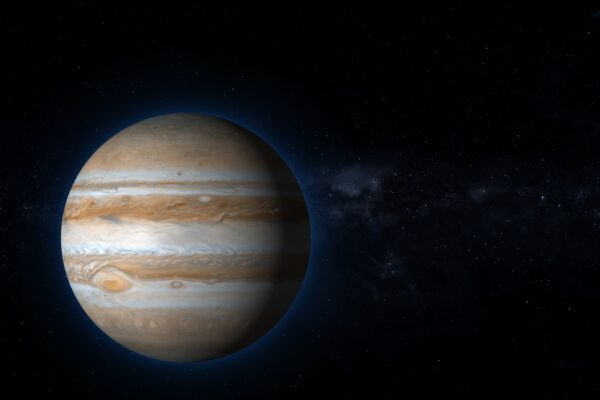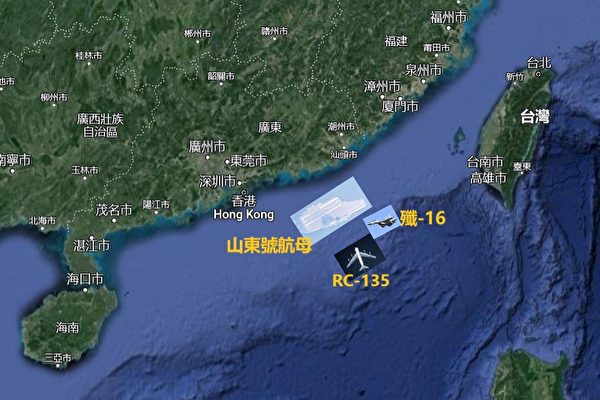【2023年11月06日訊】1977年底,李克強考入北大「七七級」法律系。
當時的北大法律系擁有良好的師資,最著名的當推學貫中西的憲法行政法學家龔祥瑞。
龔祥瑞早年專治政治學,曾赴英國深造,對西方政制、法治有親身體驗。大學期間,李克強師從龔祥瑞,很快成為他的得意門生。他專攻《外國商法》,寫出過經濟論文《經濟改革中市場的法律控制》,翻譯了《改進法律機制以適應經濟的發展》,並在龔祥瑞指導下,與楊百揆、劉庸安翻譯了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勳爵的名著《法律的正當程序》。該譯著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強是第一譯者。可見,龔祥瑞稱的上是李克強大學時代的恩師。
中共建政後,政治運動不斷,龔祥瑞挨過整,尤其是在文革中,他被打成黑幫分子,受盡折磨屈辱。文革後,他曾在《「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中,詳盡的回憶和描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所見所聞。用他文中的話說,「我在這裡只能敘述我所遭受和接觸的那一鱗半爪,好比傾盆大雨中的點點滴滴,以供後人品味,共享其中的是是非非。」
掛牌遊園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6日開始至1977年6月6日止,為期十年。從1966年6月18日起,龔祥瑞被隔離反省,就是與當時所謂「黑幫分子」在一起,像牲口一樣趕來趕去,成了北京市民來校參觀者起鬨的對象。
有一天,龔祥瑞被造反派掛上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黑幫分子×××」,在名字上用紅筆打上了「×」。敲鑼打鼓,在校園內示眾遊行。觀看熱鬧的群眾中,有他的好友高名凱的女兒高蘇(當時她是大一的學生),見龔祥瑞這個模樣,笑不遏止。龔祥瑞感覺,好像她正在告訴左右同學:掛牌遊行的法律系教授是她父親的好友。他當時心想,如果她父親在世,也會遭到同樣的厄運。掛牌遊園並沒有讓龔祥瑞傷筋動骨,他也不怨天尤人。高蘇的笑聲反而使他驟然感到這場鬧劇非凡,滑稽可笑。
隔離反省
當時,包括龔祥瑞在內,法律系全系有七、八個人被關在一個教研室裡,夜以繼日的寫檢查作交代,沒完沒了。當聶元梓名震全國的時候,北京市民蜂擁到了北大校園,群眾要見見關在房裡的黑幫分子。龔祥瑞想,大概是出於好奇吧。曾經一度是著名人士,一夜之間竟成了「階下囚」,成了另一類人種,自然成了罕見的觀賞品。一天,法律系所在地四院來了一群北京市民,他們高呼口號,敲打窗口,高喊:「黑幫分子滾出來示眾!」確有人進入院內想要打開房門,把關在裡面的人一個個揪出去批鬥。他們把門緊閉著,幾個人躲在書桌下不敢露面;窗外的觀眾狂喊猛叫,要叫他們「出來,出來」!呼叫聲越吼越大,敲門聲越敲越響。龔祥瑞怕房門被踢開,與其被動揪出,不如主動向群眾交代自己的歷史問題較為上策。
他回憶說,「當時,我確實是相信群眾的。這次運動是整走資派,整當權派,像我這樣歷史上有問題的不過是陪綁者,關係不大;為了其他人的安全,不如讓我出去轉移群眾的目標為上策。我向躲在桌子底下的難友輕聲說:『還是讓我出去向他們交代,就將人群引向院子外面去了!』桌子下面所有的人都不同意,認為:『出去你這條命就沒有了。』他們都怕被憤怒的群眾活活打死,都不讓我走。」
幸而,敲了一陣,群眾見沒有動靜,也就轉移陣地,往別處去了。一時平靜下來,他們一個個又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那天中午晚了幾個小時才回到家裡。
一身濕透
法律系的29名教師在42樓南側,背上個個掛著「黑幫分子」的牌子,姓名上打了 「×」,伏在地上拔草,旁邊有兩個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看管他們,數以千計的人圍觀,猶如動物園裡的牲口那樣,一個個成了被觀賞取笑的對象。
這天中午,在拔草完畢解甲回家的路上,龔祥瑞遇到外語系女教授俞大絪,他見她愁容滿面,一聲不響低頭走路,似有無言之苦在心頭。龔祥瑞想:這位老太太一定感到被侮辱了,以往那種自信的神態在她身上消失了。結果就在那天晚上,她服了安眠藥自盡了。
在校園裡拔草,是運動初期懲罰黑幫分子的一種辦法。校園內凡有草的地方幾乎全被他們這幫人拔了個精光。一天下了大雨,全身淋得濕透,衣服也還沒換掉,紅衛兵就把他們召集起來,談談雨中勞動的感想。好在是夏天,全身濕透的身子邊談邊幹了。大家談的都是好話,有的說:「這陣大雨把我們身上的臭氣都淋掉了!」有的說:「很痛快,好比洗了個澡!」有的說:「把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清洗了一遍!」如此等等,引起紅衛兵的笑聲和讚賞。
他們說,「走吧,有收穫就好!」
一次毒打
在展覽「稀有動物」的同一會場上,原是外國留學生的宿舍樓,有個60平方米的會場。那天或許是井岡山兵團召開批鬥會。本無龔祥瑞的,他正在38樓應召交代問題以免挨鬥的一項有意安排,不知怎的又被叫去參加。當他被帶入會場時,系裡的挨鬥對象多半肉體上已被打得面目全非了,有的躺倒在地,動彈不得。他不知道前因後果,只見前面是黑漆漆的人群,有站著的,有坐著的,群情激昂,不由分說。在這種氣氛下,本能的低下頭來,無可奈何的任人「擺布」了,連思維能力也喪失殆盡,唯有任人宰割。
一陣眼花繚亂,龔祥瑞只見一個青年舉足猛然踢自己一腳,並說:「我這雙新皮鞋是專門買來踢你們這幫『壞蛋』的。」這一腳踢在龔祥瑞的左腿上,其用力之大,已使他站立不穩,似乎立刻就要往後倒下了,竟然還敢「站穩」,那雙黑色的嶄新皮鞋準確的又在原來的部位上再來一腳,這次果然跌倒在地,混混然只聞一片打倒聲,另外就是身旁躺在地上的人的微弱的呻吟聲。不久就散會了,人群一個個呼嘯而去,剩下來七八個挨打的人躺著起不來身。年輕些的陸續從地上爬起來,企圖往外走,一個個勉強站起來走到過道上,還沒有到樓梯就站立不住,個個又扶著欄杆席地而坐或半躺了下來,稍事休息想恢復體力。被毒打成這個樣子,還是第一次。人們不能理解這是為了什麼。都失去了理性。
「我們眼前的打手難道是『新中國』培育出來的?不!人有時比野獸更殘酷。」 龔祥瑞心想。
待他們一個個一拐一拐從樓梯上半爬半走下樓時,有的就只能朝著校醫院的方向走去。等龔祥瑞慢慢移走回到家裡,脫掉鞋子和襪子,將褲腳筒捲起來時,才發現自己左腿上一塊肉竟被踢了下來,四周皮肉都是青腫的。
龔祥瑞嘆道,「這樣的鬥爭看來是一個可悲的誘餌,作為治國之道並非一無所獲,我活了那麼多年,竟從未知道人間還有如此殘酷的行動。只有通過掉了塊肉才能取得這樣有益的學問,只有被打才能了解人性——個體的皮肉之痛和精神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