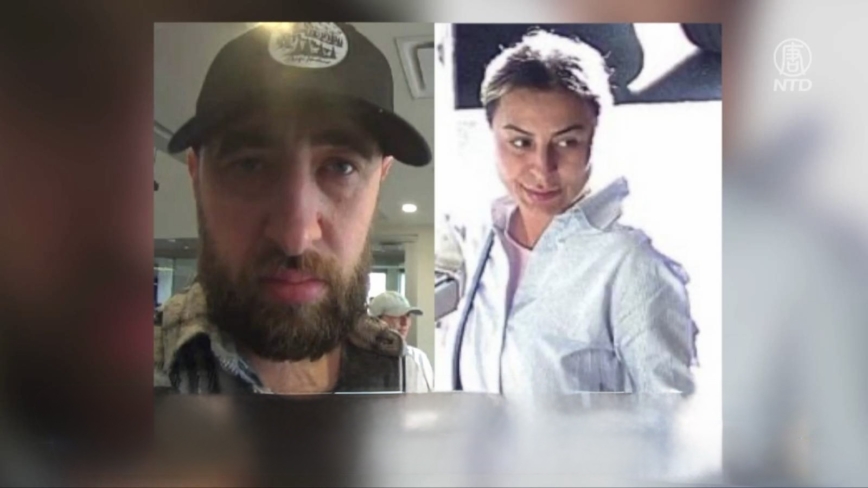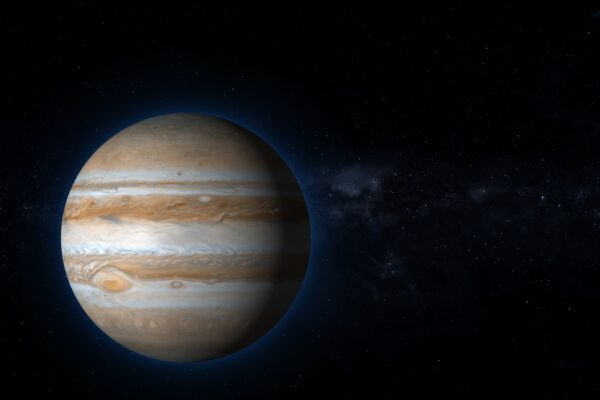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2023年12月06日訊】
徐志摩是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新月派詩人的代表之一。
他1897年出生於浙江海寧一個富商之家;1931年在從南京飛往北京的途中墜機身亡,時年34歲。
他以詩、情聞名於世。許多人有所不知的是,他還是中國最早洞悉蘇共邪惡的思想者之一。
1917年俄國十月政變後,列寧領導的俄共(布)兩次發表宣言: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在中國攫取的一切利益。
這個「空頭支票」,在當時令許多中國人,包括孫中山,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對蘇俄心生好感。
在蘇俄的遊說下,孫中山開始「聯俄」,知識界出現「走俄國的路」的呼聲。一些從蘇俄旅行歸來的人,寫了不少讚美蘇俄的文章。徐志摩也一度被蒙蔽。
但是,1925年,他親自遊歷蘇俄後,對蘇共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關於蘇俄,他做了兩件重要的事:一是寫了一本《歐遊漫錄》,記錄了他在蘇俄的見聞與觀感;二是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主編《晨報 副刊》期間,發起了一場關於蘇俄問題的大討論。
他對蘇俄的真知灼見,集中體現在《歐遊漫錄》和《晨報 副刊》的相關文章中。
他見證了蘇聯人民的困苦
他寫道:「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況益發明顯。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襤褸的小孩子,從三四歲到五六歲,在站上問客人討錢,並且也不是客氣地討法,似乎他們的手伸了出來,決不肯空了回去的。」
「不但在月台上,連站上的飯館裡都有,無數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麼來的,全靠著我們吃飯處的木欄,斜著他們呆頓的不移動的眼,注視著你蒸汽的熱湯,或是你肘子邊長條的麵包。他們的樣子並不惡,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陰沉。看見他們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問,這裡的人民知不知道什麼是自然的喜悅的笑容。」
在一個車站下車,天已經黑了,車站上照明的卻是幾隻貼在壁上的油燈。昏暗的候車室裡是滿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氣味!悲憫心禁止我盡情的描寫;丹德假如到此地來過,他的地獄裡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到了莫斯科,他看到的依然是貧窮和蕭條:大街兩旁古老的店鋪大都倒閉,漂亮的店鋪見不到了,最多也最熱鬧的是食品店,是政府開的,物資奇缺且昂貴。俄羅斯人曾有的貴族氣徹底不見了,街上走過一群群男人,卻見不到一件白色的襯衣,更不用說禮服和鮮豔的領結了。
由於蘇俄對知識分子採取嚴厲政策,「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則在經歷著政治和思想風暴的同時,體驗著經濟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種種困境」。
他發現「俄國的文化是盪盡的了」
他痛惜地看到,俄國的傳統文化正在被鏟除。
「在這大火中最先燒爛的是原來的俄國,專制的,貴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t regime(舊秩序),曳長裙的貴婦人,鑲金的馬車,獻鼻煙壺的朝貴,獵裝的世家子弟全沒了,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小說中的社會全沒了。」
那些在大火中逃難到西方的俄國人,「他們,提起俄國就不願意。他們會告訴你,現在俄國不是他們的國了,那是叫魔鬼占據去的。」
「我在京的時候,記得有一天,為《東方雜誌》上一條新聞,和朋友們起勁的談了半天,那新聞是列寧死後,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訴,被告是骨頭早腐了的托爾斯泰,說他的書,是代表波淇窪(資產階級)的人生觀,與蘇維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寧臨死的時候,叮囑他太太一定要取締他,否則蘇維埃有危險。法庭的判決是列寧太太的勝訴,宣告托爾斯泰的書一起毀版,現在的書全化成灰,從這灰再造紙,改印列寧的書,我們那時大家說這消息太離奇了,或許又是美國存心污毀蘇俄的一種宣傳。」
為了解托爾斯泰的書是否真的被禁毀了,他在莫斯科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問及那則新聞,托爾斯泰小姐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現在托爾斯泰的書買不到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書也都快滅跡了。
他問:莫斯科還有哪些重要的文學家?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他寫道:「假如有那麼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書,算是托爾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訴你:不但他的書再也買不到,你有了書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樣?」
「假如這部分的個人自由有一天叫無形的國家威權取締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樣?」
他目睹了蘇俄對資本主義的仇恨
在莫斯科期間,他看過一部戲劇,舞台正中懸掛著一隻「可怖的大手」,象徵命運或是資產階級,舞台上頻繁出現各式各樣的鬼和屍體,讓他感覺這個戲如同一場「怖夢」。
戲的主題是揭露資本主義的黑暗,社會沒有前途,生命沒有意義,工人、醉漢、賣淫女、強盜、孩子等下層人民都有相同的命運:要麼在階級壓迫下生不如死,要麼在革命中死去並獲得永生。
戲劇讓他壓抑,他到墓園懷古,卻發現很多貴族的墓遭到損壞,「不少極莊嚴的墓碣倒在地上」,「好幾處堅緻的石欄與鐵欄」被砸毀。此情此景,令他慨嘆:「階級的怨毒在這墓園裡都留下了痕跡。」
他窺見了蘇共製造謊言的把戲
英國著名作家韋爾斯1920年在蘇俄親歷了這樣一件事:參觀一所小學校時,韋爾斯問學生平時學不學英文,學生一齊回答:學。韋爾斯又問:你們最喜歡的英國文學家是誰?學生一齊回答:韋爾斯。韋爾斯進而再問:你們喜歡他的什麼書?學生立即說出了他的十多種著作。
韋爾斯不相信自己能夠如此為俄羅斯孩子所熟知,覺得這這些學生是被訓練出來的。於是,他獨自悄悄來到一所更好的學校,把那些問題重新問了一遍,得到的回答卻完全不同——孩子們對韋爾斯一無所知。韋爾斯又來到該校藏書室,書架上沒有他的任何著作。
韋爾斯明白了:原來一切都是演戲。
讀了韋爾斯的故事後,徐志摩總結說:「蘇俄之招待外國名人,往往事前預備,暴長掩短。」
他發現蘇俄教育是「黨化教育」
當時,中國有一些人,如胡適推崇蘇俄的教育。
徐志摩寫道:「就我所知道的,他們的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他們側重的:第一是宣傳的能力;第二是實用的科目。例如化學與工程。純粹科學與純粹文學幾乎占不到一個地位。宗教是他們無條件排斥的……但他們卻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階級戰爭唯物史觀一類觀念來替代信條。」
他認為,蘇俄的「黨化教育」是「中世紀政治的一個反響」。「有觀察力的人到過俄國的,都覺得俄國的新政治是一種新宗教;不論他們在事實上怎樣的排斥宗教,他們的政治,包括目的與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紀的教會性的。」
「你沒有選擇的權利,你只能依,不能異。」「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他認為列寧是一個心硬似鐵的危險人物
1926年1月,他編《晨報副刊》時,陳毅給他寄來一篇文章《紀念列寧》,想在晨報發表。但他沒有發表,卻自己寫了一篇《列寧忌日——談革命》發表了。
他寫道:「(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這個革命是出於一種階級戰爭的學說,它的目的是要抵達一種烏托邦式的人類大同。
「我卻不希望他(列寧)的主義傳布」,因為「我怕他」。「他生前成功是一個祕密,是他特強的意志力,他是一個Fanatic(狂熱分子)。他不承認他的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他是一個制警句、編口號的聖手;他的話裡有魔力——這就是他的危險性。」
列寧及其追隨者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天堂的中間卻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徐志摩為什麼能識破蘇共的邪惡?
在21世紀的今天,回過頭來看一看徐志摩上世紀20年代對蘇共邪惡的認識,不能不說他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罕見的有先見之明的人。他什麼能做到這一點呢?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與他的「單純信仰」有直接關係。
民國大師胡適這樣評價徐志摩:「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裡,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
徐志摩的「單純信仰」來自哪裡?來自他受到的西方自由、民主、博愛的教育。
他在國內讀過的大學有:滬江大學,上海浸信會學院,北洋大學,北京大學;在國外讀的大學有:美國麻州的克拉克大學;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劍橋大學國王學院。
他任教過的大學有:在北京大學、光華大學、東吳大學、大夏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女子大學。
他在上海就讀的兩所大學都是教會大學;他在天津上的北洋大學,是中國洋務派辦的大學;他上北京大學時,校長是從西方留學歸來,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辦學宗旨的蔡元培。
他在美、英留學時,與許多崇尚自由、民主的作家、藝術家、教授有過交往。他在國內工作的大學,大多有西方文化背景。
這樣的教育背景,加上他熱愛自然、自由、美好的天性,使他直面蘇俄的陰暗、冷酷、血腥時,他就會本能地感到不適、反感、厭惡,並希望從心底遠離他。
第二,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影響。
徐志摩崇拜羅素。1920年,他放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不讀,橫渡大西洋,到英國去追隨羅素。
俄國十月政變後,羅素推崇過蘇俄。但是,1920年,羅素隨英國工黨代表團訪蘇歸來後,寫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一書,從「蘇俄的積極擁護者」轉變為「蘇俄的堅定批評者」。
羅素的新書出來後,徐志摩不但做了筆記,還寫了評論。他雖不完全認同羅素的看法,卻也不能不受其影響。他在書評中說,羅素之所以拒絕蘇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布爾什維克的方法實現共產主義,人類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巨大代價,它所要達到的結果能否實現,也是未知數。
就前者而言,它太殘酷;就後者言,它太虛幻。為了實現那個虛幻的烏托邦,採用慘烈的暴力手段,讓人類付出慘重的代價,這是羅素害怕的。
羅素不滿於人類的生存現狀,但他拒絕流血。他致力於救渡人類,但救渡的辦法,應是漸進的、和平的。這些都對徐志摩產生了影響。
結語
1925年,徐志摩在莫斯科參觀了列寧遺體展覽館。他進門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個通體血紅的地球儀,立即感到震驚與恐懼。他寫道:
「從北極到南極,從東極到西極(姑且這麼說),一體是血色,旁邊一把血染的鐮刀,一個血染的錘子。那樣大膽的空前的預言,摩西見了或許會失色,何況我們不禁嚇的凡胎俗骨。」
徐志摩發出這樣的警告:「旅行人!快些擦淨你風塵眯倦了的一雙眼,仔細的來看看,竟許那看來平靜的舊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種,留神!回頭地殼都爛成齏粉,慢說地面上的文明!」
當時,徐志摩的警告,許多人都聽不進去。
但是,在隨後的幾十年間,共產主義運動製造的「血污海」,不但淹沒了蘇聯、東歐,還淹沒了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柬埔寨等。
大紀元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