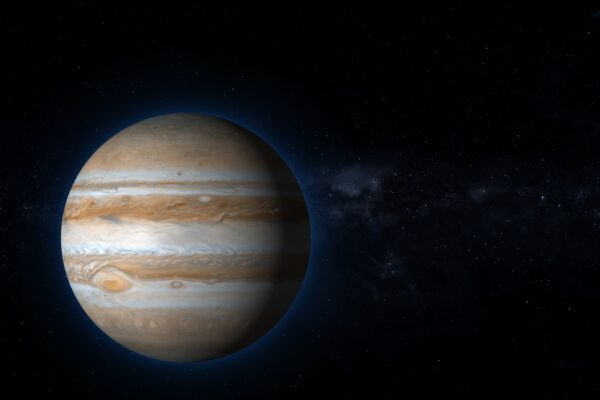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2023年12月15日訊】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死後一個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發動了軍事政變,逮捕了替毛效力的「四人幫」,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與此同時,亦開始對「四人幫」的追隨者展開了清洗。
1980年,中共最高法院成立的特別法庭對「四人幫」進行了所謂的作秀式公開審判,認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將文革的罪責推到他們身上,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
根據後來披露的庭審記錄,一起在北京軍事政變之後的上海的未遂武裝政變浮出水面。
王洪文承認意圖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1980年12月13日,王洪文、張春橋出庭接受審訊。庭長江華,副庭長兼第一審判庭審判長曾漢周,審判員共十五人。出庭的中共檢方人員為廳長黃火青,副廳長喻屏和檢察員三人。
法庭首先就起訴書中指控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以上海為基地,抓武裝力量,在面臨覆滅之際,策動武裝叛亂一事」,並首先對王洪文進行審問。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都是時任上海書記,排名不同,後兩人還兼革委會副主任。
王洪文承認在1967年接受張春橋的指令,在上海建立了由他們控制的武裝力量。王提到張春橋曾說「軍隊不能領導民兵,民兵的領導權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裡」,因此作為上海工總司頭頭的王洪文奪取了上海警備區的民兵領導權,權力掌握在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手中。
王洪文還就自己對王秀珍等人所說的「軍隊有問題,路線不端正,是靠不住的」進行了解釋,稱是因為當時上海警備區有兩派,這兩派中間,實權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這一派手裡的。至於說的「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裡,軍隊裡沒有我們的人」則是一方面指上海的軍隊,一方面指北京的鄧小平。
根據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的供詞,王洪文還在1975年9月,召集市民兵指揮部頭頭開會,並說「誰要一個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後我再把民兵拉起來」,他還說要「準備上山打游擊」。
張春橋對指控沉默以對
在庭審張春橋時,對於審判員詢問的「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指示王洪文在上海建立自己控制的武裝力量」以及馬天水等人的關於張春橋、王洪文將「民兵緊緊控制在自己手裡,完全脫離警備區的領導,不和軍隊發生任何聯繫」等問題,張春橋皆緘默不語。
不過從審判員的一系列問詢中,可知在1976年6月27日,毛快死前,上海民兵指揮部申請發槍,但報告一直未批下來,馬天水得知後,找到有關人員訓斥,並立刻批了「立即發」三個字。按照馬天水的說法,之所以急於發槍,是因為擔心在毛病重期間發生內戰,因此需要加強民兵力量,提前做準備。
據說最後一次民兵獲得了半自動步槍三萬五千支,另外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
徐景賢還作為人證出現在法庭上。他提到,1976年9月21日,毛剛死十幾天,他借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面匯報了幾件事,一是在8月與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密談後,丁盛覺得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而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張春橋等要有所準備。他還告訴張春橋,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枝。徐景賢說張春橋聽的很仔細,還問了一些問題。
幾天後,也就是9月28日,張春橋派王洪文的祕書肖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傳話,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六個市委常委。
張春橋說,「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挂帥……我不是一個憂天派,但是有點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受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從張春橋的言辭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共高層內部博弈激烈,打仗也很有可能無法避免。
不過,被中共認為「在策劃武裝叛亂這個問題上負有主要的罪責」的張春橋,從庭審記錄中看,並未承認所指控之事,基本保持沉默。
未遂武裝政變
庭審記錄顯示,10月7日,毛死後一個月,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司令周純麟接到通知,讓他們到北京開會。這引起了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等人的警覺,認為這很反常。
在馬天水、周純麟去北京之後,徐景賢和王秀珍就開始到處打聽有些什麼動向。當晚,徐給當時的江青的紅人、文化部部長於會泳打了電話,接著又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詢問北京的情況。其後,又與馬天水的祕書房佐庭通了電話,但房佐庭說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
忐忑不安中過了10月7日後,8日一大早,徐景賢和王秀珍就聽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說,張春橋的兒子原定8日上北京的,結果李文靜給張春橋打了一夜電話沒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此時的張春橋其實已經被華國鋒、葉劍英等人抓捕。
聽李文靜這樣說後,內心不安的王秀珍馬上親自給王洪文打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同樣打不通。徐景賢和王秀珍商量後,將張春橋在上海的祕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祕書廖祖康和肖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向北京打電話,這幾個人到來以後,就通過各種渠道,用各種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那裡打電話,結果一個都打不通……
徐景賢於是又給《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打了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魯瑛十分反常,沒有講兩三句話就急忙把電話掛上了。
也是在這個時候,徐景賢和王秀珍又收到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通知裡面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上海警備區也匯報說,原來總政決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現在通知停止召開。
無疑,北京可能出大事了。這讓徐景賢等人很是憂慮。徐與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何秀文、肖木、廖祖康聚在一起分析形勢,揣測究竟是什麼人出了事。
此時,市委常委張敬標通過上海警備區的軍用電話接通了北京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祕書房佐庭。房佐庭告訴他們說,會議不准往外打電話,又說這次他們到北京的時候是穿軍裝的人去接他們的。房還說了一句暗語「我的老胃病重患了」。
撂下電話,幾個人推測沒有胃病的房佐庭說這句暗語究竟是何意思。王洪文的祕書廖祖康說:「幾個老帥,像葉帥、徐帥他們還是有號召力的。」大家於是都明白可能是幾個老帥已經動用軍隊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下手了。
幾個人瞬間明白形勢非常嚴重,於是他們分別去找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市公安局負責人、新聞界負責人,為武裝政變提前打招呼和吹風。
當晚,王秀珍告訴徐景賢說,她和上海革委會副主任金祖敏的祕書繆文金約好了,下午要繆文金乘飛機趕到北京去摸情況,如果摸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話,就打電話傳一句暗號來,說「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說,剛才繆文金已經打來了電話,傳來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號。
徐景賢聽罷心裡一驚,「果真出事了」。他想到張春橋9月28日的預言果真應驗了,他所說的大考驗的時刻真的來到了。他馬上給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打電話,證實了文化部的于會泳、錢浩亮、劉慶棠他們幾個人和江青之間的電話聯繫也中斷了。大家於是議論紛紛。
正在這個時候,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公安部準備當公安部副部長的祝家耀打來電話說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這樣就進一步證實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統統都被抓起來了。
過了一會兒,劉慶棠又打來了電話,暗示文化部的幾個人也被抓了。聽罷,肖木驚叫起來,說:「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肖木這麼一說,大家一片混亂,生怕有人來抓。
下一步怎麼辦?徐景賢等人聚集在一起商量對策,最終決定發動武裝政變。依據一個是張春橋9月28日下的指令,即「有人要搞上海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實力,我們的實力就是上海民兵」;一個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論。
姚文元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就總結說,「天安門事件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必須以革命的暴力來對付與鎮壓反革命的暴力。這種鬥爭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們今後也要堅持這樣一條基本經驗」。對此,徐景賢深以為然。
王秀珍告訴大家,她白天已經與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等幾個人談過了,帶槍的武裝民兵有兩千五百人在各工廠集中,可以隨時拉出來,另有三萬一千人分散待命。
市委常委王少庸認為,光靠民兵還不行,要有部隊一個團的力量才能形成一個拳頭。王洪文的祕書廖祖康於是說,我們要把警備區的幾個負責人帶在我們身邊,因為靠我們去調動部隊是調不動的,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調動部隊。
很快,徐景賢和王秀珍等約談了上海警備區參謀長、副司令員張宜愛,上海警備區警備師師長李仁齋等人,確定了以警備師作為主要武裝力量,策划上海叛亂。
按照徐、王等人擬定的計劃,確定了兩個指揮中樞,一個由徐景賢負責抓總和準備輿論,地點定在華山路丁香花園。其他負責人還有市委常委王少庸、張宜愛、張敬標、朱永嘉、李仁齋等人,警備方面由李仁齋負責。一個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後轉移到東湖路招待所。其他參與人員有市委常委馮國柱,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楊新亞,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
此外,在策劃會上,廖祖康還提議,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他們,都找在一起,說是這樣可以調動工人隊伍。這件事情由其負責。
眾人商議妥當後,在分手前,徐景賢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政變」手令。具體內容是:「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三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即晩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
不久,徐景賢又寫下第二號手令,內容是:「電台由李仁齋同志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像賢同志的指揮。三連由李仁齋同志告知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劉像賢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當時調到人民廣播電台擔任黨委書記。
隨後,在李仁齋的調遣下,警備區的兩個連隊,分別進入上海市委和廣播電台維持秩序。
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副組長施尚英在法庭上也證實,10月8日晚,民兵第一批集結的有3240人和摩托車100輛、卡車100輛,配正、副駕駛員,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十五瓦電台15部,祕密指揮點設在江南造船廠和國棉十七廠或國棉三十一廠,他們還要求各個區的民兵指揮部的頭頭全部在位值班,且在9日十八時以前,全部落實。
就在上海各地區的民兵力量逐步完成集結,上海武裝政變一觸即發時,徐景賢和王秀珍也接到了赴北京「參加會議」的通知。這應該是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為防止上海生變而採取的措施。
在徐、王去北京後,剩餘人等在焦急中等待著。12日,有人認為不能再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來做決定了,要麼大幹,要麼不干,口號是四個還我,即「還我江青、還我文元、還我春橋、還我洪文」。同時要民兵進駐電台,要電台廣播告全市人民書。還有人建議通過破壞電網,將上海搞癱瘓……在嚷嚷聲中,大家同意武裝政變繼續,並制定了「捍一」、「方二」兩個武裝政變的方案。
「捍一」的主要內容是:控制首腦機關、報社、廣播電台、橋梁、車站、碼頭、機場和交通要道;確定指揮核心人員名單:開設指揮所;兵力部署;重點「支援」地域和反空降;口令、暗令、標記;彈藥補給和武器修理;加強社會面的控制等。
「方二」的主要內容是:從上海外圍到市中心區設立三道「控制圈」;在上海與江蘇、浙江交界處,設六個控制點,為第一控制圈;市區設兩道控制圈;並規定了各區、縣的任務和預備隊的組成。
另外還有通信保障計劃,規定了通信任務和多種通訊手段。
不過,顯而易見,這場缺乏民意基礎、缺乏某個在任且有權勢的高層支持的武裝政變,夭折並不令人意外。
也是在10月12日,北京高層也在玉泉山召集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上海問題,並決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將軍蘇振華和倪志福、彭沖為核心的中央工作組到上海。
10月13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到了上海。他們在市委常委會上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的情況。而且此時,「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已經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上海。
一週後,即10月20日晚上,蘇振華等人祕密前往上海,並在海軍上海基地司令員杜彪、政委康莊等的護衛下,離開機場,下榻在水電路的海軍上海基地。蘇連夜召集了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和駐滬陸海空各部隊負責人,了解情況,進行布置。
次日,蘇除了找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談話外,還將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找來,將參與政變的軍方人員統統調回去,並請上海警備區司令周純麟直接抓民兵。南京軍區又派了副參謀長張挺,作為工作組成員,監管民兵指揮部。
上海武裝政變就這樣流產了。不久後,蘇振華被任命為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倪志福是第二書記,彭沖是第三書記。此後繼續就政變抓捕、審查一些人。
雖然上海武裝政變貌似一場鬧劇,但也反映了中共高層博弈的激烈。北京以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為首的一派在與張春橋「上海幫」的較量中,取得了勝利。或許這也是天意使然。如果江青、張春橋等人繼續掌握權力,繼續維持毛的專制統治,忍受不下去的中國人是否會選擇推翻這個政權呢?而鄧掌權後的所謂改革開放,只不過是替中共又延長了三十多年的壽命。
如今,中共再次走到了一個節點,天怒人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此時,中共黨內已無人可以為其續命,其退出歷史舞台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主要參與政變者結局
1981年,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改為無期徒刑。2005年因胰腺癌死於北京復興醫院,終年88歲。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於1992年因肝癌死於北京復興醫院,終年56歲。
1982年,徐景賢被判刑18年,王秀珍判了17年,馬天水因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中止預審。馬天水1988年12月在上海精神病院去世,時年77歲。
徐景賢於1992年6月保外就醫,1995年刑滿。2003年,回憶錄《十年一夢》在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10月31日在家中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2013年《徐景賢最後回憶》在香港出版。
王秀珍1994年被釋放。目前如果健在的話,業已89歲。
時任上海警備區參謀長、副司令員的張宜愛,被開除黨籍,剝奪軍銜。2002年離世,終年81歲。李仁齋則被保留了黨籍和軍籍。目前低調地生活在上海,如今已經是105歲高齡的老人了。
參考資料:「四人幫」庭審記錄
《末日瘋狂——「四人幫」及其餘黨策動上海反革命武裝叛亂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