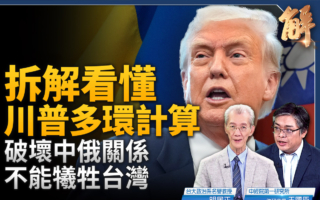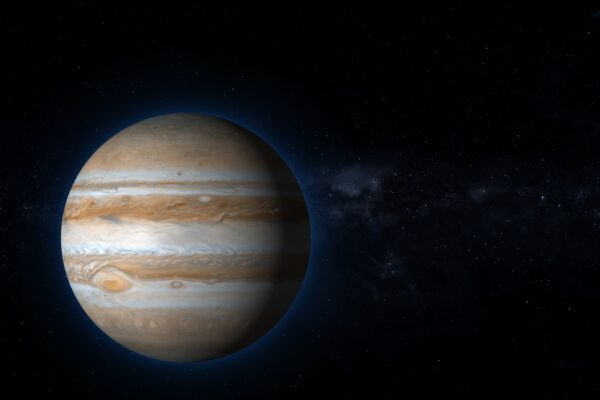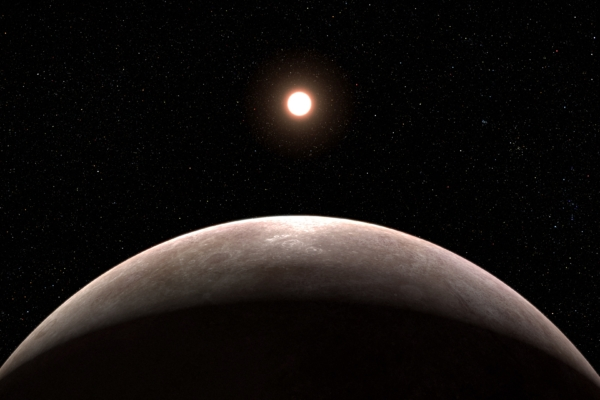譯者按:2019年,尤利婭‧孟德爾(Iuliia Mendel)在四千多名申請者的競爭中勝出,擔任了當時剛上任的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新聞祕書,任期從2019年6月3日至2021年7月9日。最近,她出版了一本書:《我們的生命之戰:我與澤倫斯基一道的時期、烏克蘭的民主之戰及其對世界的意義》(1)。以下是她在X(即以前的推特)上發布的文章,其中她簡單地介紹了自她曾祖父母以來的家族歷史(2)。
我的曾祖父曾經很富有。他擁有大量的土地,最重要的是,還有一座風力磨坊,這對麵粉的生產是至關重要的。
當共產黨人奪權之時,他說服了人們要接受這種新的政治,以便使烏克蘭成為蘇聯的一部分,而不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他認為這是他對俄羅斯帝國的崩潰所做的貢獻。
多年後,布爾什維克沒收了他的土地和財產,並宣布他是人民的敵人,當時,這是人們所能想到的最嚴重的指控。他已經是四個孩子的父親,被送到了集中營。
我不知道他在那裡待了多久,但他活了下來,回來時已經身無分文。回到家後,他發現大女兒吉娜(Zina)已被納粹帶走、送去柏林勞動。我的祖母是吉娜的妹妹,一生都在尋找她。她讓我找到有關她姐姐的信息。但我沒有那樣的機會。我不知道吉娜是否到了柏林,她是活著,還是已經去世,是怎樣的經過。
我曾祖父最小的兒子雷夫(Lev)被凍死了,因爲在冬天納粹拿走了他的床單,讓他躺在金屬板上。
我小的時候,祖父教我德語,簡單的兩句話:
舉起雙手。晚安。
即使發生那樣的事情之後,我的祖母一生都在說俄國人比德國人更懷。
說法有爭議,但可以理解。她驚恐地回憶起1930年代初史達林在烏克蘭人為製造的飢荒。人們吃狗,甚至吃自己的孩子,或者直接餓死在街上。
那年她5歲。她的名字是柳博芙(Lyubov),意思是「愛」。她有一個同齡、同名的朋友。或許那時女孩的名字就是這樣取的,希望能有一個不一樣的生活。
由於飢荒嚴重,村民們派小孩子在夜裡去偷穀穗,這樣不會被發現。他們村子裡有許多人如此倖存了下來。有一天晚上,村子裡傳著謠言說有契卡爪牙(Chekist)(3)搜查,去莊稼地裡會很危險。那天晚上,我的曾祖母沒有讓祖母出去。而祖母的朋友去田裡了,顯然她家完全沒有食物了。夜裡有人開槍。早晨,那個受傷的女孩被抬回家。我的祖母再也沒有見過她的朋友「愛」。
當我的媽媽要上大學時,她被拒絕了。因為她是人民的敵人的孫女。她就坐在大學門口的台階上,坐在那裡抗議被這樣對待。一位教授問她為什麼坐在這兒。她回答說,她會一直坐在台階上,直到被允許入學為止。
不久我的祖母接到了克格勃的電話。當她跟我講這個故事的時侯,全身在發抖。而且她必須進城去見克格勃。她不僅為自己擔心,而且更為叛逆的女兒擔心。
好在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克格勃知道蘇聯很快就會崩潰了。他們與我的祖母進行了認真的談話,並且告訴她新的時代即將到來,同時批准了我母親入學。
我的母親就是這樣成為醫生的。她在大學裡遇到了我的父親,他們在同一個村子,但是在大學相遇之前並沒有碰過面。
我出生時,母親正在讀大學的最後一年。於是她把我送到了我祖母家,在那裡我度過了人生的最初的幾個年頭。我的父母無法在札波羅熱(Zaporizhzhia)為我辦出生登記,那是我來到這個世界的地方,也是他們學習的地方。因此,我被登記在赫爾松(Kherson)地區的海尼切斯克(Henichesk)市,我的父母在那裡逗留時帶我去見了我父親的親戚們。
我不是在海尼切斯克出生,也從未在那兒居住過,但我的護照和維基百科就是這樣記載的。當我成為總統的新聞祕書時,海尼切斯克的每一家報紙都自豪地報導我。雖然這些人過去從沒見過我。
我的祖母常說,沒有什麼比戰爭更糟糕的了。令我欣慰的是她沒有看到烏克蘭目前正在經歷的事情。
我的家庭經歷了太多的痛苦,太多跨代的創傷,以至於這些依然是一個精神上的重負。
我的背上有烏克蘭的刺繡,上面是一個大大的麥穗刺青。麵包對我的家人來說一直是重要的。我明白我的祖母為什麼那樣討厭俄國人。
但烏克蘭人一直在戰鬥。我們值得有機會終於開始建立一個實現精英管理與平等的、充滿機會與安全的未來。在我的國家構築一個職業生涯比在西方國家要困難得多。然而相當多的窗口已經打開,諸多的聯繫管道已經建立,然而也犧牲了太多。烏克蘭必須成為一個成功的國家,民主一定要獲勝。爲烏克蘭站出來(#StandForUkraine)的我,是為了銘記我的家人,糾正他們的過錯,治癒他們的痛苦,從而創造未來。
這是我的奶奶和6個月大的我,在我們的房子裡,第二張照片上你看到房子現在的樣子。安息吧,奶奶。


註:
(1)https://www.amazon.com/gp/aw/d/1668012715
(2)https://twitter.com/IuliiaMendel/status/1705406808171429968
(3)Chekist是指蘇聯契卡(Cheka)的秘密警察,契卡後來演變爲克格勃(K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