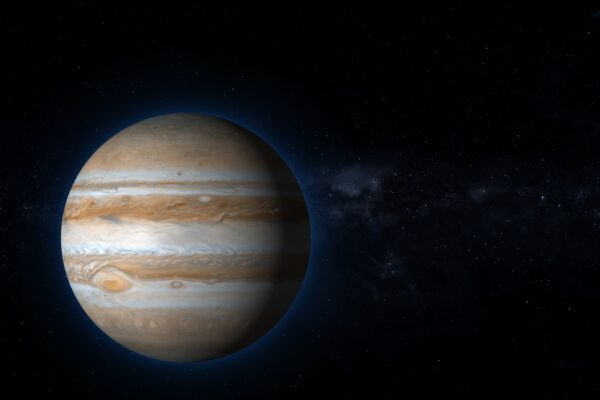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2025年04月29日訊】(Amy Denney報導/大紀元記者王月編輯)處於青春期前期的索菲婭(sofia)從未真正覺得自己融入了這個階段,於是她轉向了一個可以迷失自我、令人麻木的地方。
她一小時接著一小時、一天接著一天地盯著智能手機不停地滑動,試圖尋找自己的身分。這讓她輕鬆地轉移了注意力,逃避新冠(COVID,中共病毒)疫情隔離造成的社交孤立感以及父母離婚帶來的痛苦。
「我當時完全被手機裡的世界迷住了。」如今15歲的索菲婭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說。她被自己認為無法達到的(網上宣揚的)標準所迷惑,她開始討厭自己,甚至真心害怕與同齡人交談。
「隔離結束後,每次外出,我都會出一身大汗」,她說,「我會很緊張,與人交談時臉都在發燙。」
她不會談論自己的感受,而是任由它們在心裡積壓,直到某一時刻情緒爆發。
索菲婭開始思考自己的選擇。她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同齡人炫耀自己服用治癒焦慮的藥物,同時也看到了他們越來越沉迷於無節制地刷手機。像索菲婭一樣,如今的青少年很容易陷入社交媒體設下的陷阱,這些社交媒體助長焦慮和抑鬱,並且培養他們去相信藥物治療,認為藥物是擺脫青春期不適感——有時就是些正常的情緒反應——的唯一方法。
像TikTok(抖音國際版)這樣的社交平台放大了用藥物治療青少年焦慮與抑鬱的各類主張。這些主張包括精神科醫生普及藥物知識、網紅發布贊助內容、醫藥公司投放廣告,甚至還有青少年炫耀自己獲得的抗焦慮處方藥。
青少年的焦慮:過去與現在
如今,關於治療焦慮的醫療化信息鋪天蓋地,這與兩代人之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之前,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SSRI)剛剛進入市場,用於治療抑鬱和焦慮。藥物治療在當時還屬於相對陌生(且通常是私下裡進行)的應對心理健康的解決方案。
社交媒體提高了人們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認知度和接受度。然而,專家們也擔心,人們對藥物快速見效的關注是片面的,這反而干擾了預防焦慮與抑鬱的正常努力,也影響了更全面的心理健康的治療方案。
研究顯示,抗焦慮和抗抑鬱藥物所帶來的風險——如藥物依賴性和耐藥性、服藥過量和自殺傾向——正在青少年中上升,而心理治療卻變得越來越不常見。
「在美國,製藥公司投放了大量的廣告宣傳談論精神健康問題」,獲得認證的精神科醫生、專門治療精神藥物副作用的約瑟夫‧維特-多林(Dr. Josef Witt-Doerring)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表示,「這些宣傳使青少年不太接受焦慮是應對壓力的合理反應,反而更傾向於將其視為一種身體上的疾病。」
「因此,要麼是醫生主動給他們開藥,要麼是他們自己去找醫生,說:『我有(心理健康)問題,我需要藥物。』而這一切,在社交媒體的影響下,被進一步放大。」
維特-多林醫生指出,焦慮對處於人生過渡期的青少年和年輕人來說,是非常正常的(情緒反應)。
然而,維特-多林醫生也指出,青少年尤其容易陷入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自己大腦中存在化學物質失衡。他表示,目前並沒有任何檢測能夠準確評估與抑鬱和焦慮相關的神經遞質的含量,也沒有證據表明藥物可以修復這種(化學)失衡。
算法推波助瀾
《教育週刊》(Education Week)是一份面向教育工作者的出版物,其調查發現有大量證據表明,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作為診斷自己和同齡人心理健康狀況的平台。
調查發現:
• 65%的學校領導和教師報告稱,學生有時或經常使用社交媒體來診斷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
• 55%的高中生承認至少有過一次使用社交媒體來診斷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28%表示他們有時會這樣做,10%表示他們一直這樣做。
根據《歐洲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Europea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的一項系統性綜述,TikTok上觀看量最高的內容中,近一半圍繞著心理健康不良這一主題,並使用「心理健康」關鍵詞作為標籤。
研究發現,流行的心理健康話題——尤其是關於抽動症、分離性身分障礙和自殘行為的話題——與治療這些病症數量的上升存在關聯。
維特-多林醫生表示,TikTok已讓青少年用戶將他們歸屬於與其他青少年和名人共同與焦慮和抑鬱作鬥爭的某一社群,視為一種榮譽徽章。
「網上有大量內容在講,『這就是一個患有重度抑鬱障礙的人的一天,這些都是我正在服用的藥物。』」他說,「這真的讓人覺著,這麼做是極其正常的。你看到得夠多,就會覺得:『噢,原來每個人都有這些大腦疾病,大家都需要吃這些藥。』」
TikTok沒有回應《大紀元時報》就此事的置評請求。
社群媒體對年輕女孩的影響尤其讓24歲的研究生艾莉婭‧基西克(Aaliyah Kissick)感到擔憂,她曾擔任青少年輔導員。
「這些帖子很具有說服力,真的讓人驚訝。」她告訴《大紀元時報》,「對大腦還在成長期的人來說更危險,因為這些內容是基於評論進行定位投放的。」
她表示,TikTok演算法不僅推送用戶本身關注的內容,還會展示他們的朋友正在觀看的視頻。青少年可能只是因為朋友在關注抗抑鬱藥左洛復(Zoloft)的相關內容,就會被同類視頻轟炸。
「不幸的是,如果一群人聚在一起討論精神疾病,但反覆沉溺於談論各種症狀,而不是尋求解決辦法,那就容易形成一種回音室效應,讓大家的病情變得更加嚴重。」她說。
過度依賴藥物治療
家庭醫生兼綜合醫學治療師卡米‧本頓醫生(Dr. Cammy Benton)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表示,當前許多治療青少年焦慮的方法忽視了其背後更複雜的根源性因素,例如學業壓力、社交動態關係、家庭不穩定以及未被診斷出來的學習性障礙。這些根本性問題往往需要一種更全面的、發展性的處理方式,而不是立刻使用藥物進行干預治療。
她指出,日益增長的藥物處方治療趨勢,可能會在無意中掩蓋這些深層次的問題,有可能阻礙青少年發展關鍵的應對機制,並阻礙他們理解造成自己心理健康問題的背景根源。
數據顯示,在2020年,近12%的兒童被醫療專業人士告知患有抑鬱或焦慮症,而在四年前,這一比例為9.4%。
根據《兒科學》(Pediatrics)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青少年在就診時提出焦慮相關問題的比例從2006年的1.4%上升到2018年的4.2%,增長了三倍。該研究是基於「國家門診醫療護理調查」(National Ambulatory Medical Care Survey)中關於青少年就診的相關數據。
在同一時期,青少年的焦慮症確診率增加了三倍,同時也是年輕人確診率的近三倍。但是,接受心理治療的人數比例卻從49%降至33%。
在被診斷為焦慮症的青少年中,約有62%接受了藥物治療,其中45%使用了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SSRI),18%使用了苯二氮䓬類藥物(benzodiazepines,又稱苯駢二氮雜䓬類)——後者可能存在危險性。此外,兒童精神科醫生更可能在高收入的縣、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社區以及大都市開設門診,而非周邊地區。換句話說,地區之間的差異也限制了青少年獲得這些醫療服務的機會。
SSRI類藥物——尤其是百憂解(Prozac)、來士普(Lexapro)、西酞普蘭(Celexa)和左洛復(Zoloft)——是治療焦慮的一線藥物,通常與「認知行為療法」(CBT)共同使用。CBT是一種心理治療方法,旨在幫助青少年識別不良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並制定更好的應對策略。

發表在《兒科學》期刊上的論文作者寫道:
「在就診過程中,心理治療的減少以及對焦慮症藥物依賴的增加,可能反映出,在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日益加劇的背景下,門診醫療資源持續緊張的問題。」
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與兒童精神科醫生地區性短缺有關。另一份《兒科學》上的報告指出,儘管這一專業領域在增長,但實際的就診並沒有改善。在2007年和2016年,美國有70%的縣沒有兒童精神科醫生。
任何能夠開處方藥的醫生都可以為青少年開具SSRI或其它抗焦慮的藥物,美國心理學會(APA)認為這些藥物是安全的。不過,該協會並未回應《大紀元時報》就此事發出的評論請求。
精神科醫生維特-多林指出,醫生們可能不會主動告知(藥物的)副作用,是因為他們認為副作用很少見。與此同時,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也不會討論心理治療、運動、充足睡眠或健康飲食——而這些其實是導致心理健康狀況不佳的基本因素。
精神病學教授羅傑‧沃爾什(Roger Walsh)在一篇發表在美國心理學會的文章中寫道:「生活方式的改變能為病人、治療師以及整個社會帶來顯著的療效,但這種(治療)方法仍然被嚴重低估,且在教育和臨床實踐中使用不足。」他建議的生活方式調整包括:健康飲食、親近自然、規律運動、參加宗教活動以及休閒娛樂。
維特-多林醫生認為,特別對於青少年來說,藥物應當是最後的選擇,只有在遭遇極端痛苦時才使用。他警告說,急於通過藥物尋找快速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在玩一場俄羅斯輪盤賭遊戲。
「如果整個醫療系統只是以一種交易式的方式來對待病人,每次就診只有15分鐘,只聊藥物,而不去真正幫助患者解決問題的根源,那就是個大問題。」他說,「這樣下去,最終的結果將是,很多人開始吃藥,但卻無法停藥。」
青少年焦慮的治療,在制定與執行之間存在差距
治療青少年焦慮和抑鬱複雜化的原因是:他們通常在藥物服用或行為改變方面堅持得並不好。像是情緒成熟度、發育期,以及家庭的系統支持等因素都會影響他們是否願意堅持完成治療計劃。
「其實不管什麼年齡,養成良好習慣都是一件很難的事。」家庭醫生卡米‧本頓說道。
針對那些在執行治療方面比較複雜的病例,她表示自己更傾向使用磁共振療法(magnetic resonance therapy),這是一種「經顱磁刺激」(TMS)技術,已經在治療焦慮方面表現出一定的潛力。治療過程是將磁脈衝定向地發送到大腦的特定區域。
「這類治療不需要他們的執行力」,本頓醫生解釋說,「因為,讓他們按照你說的去做,真的太難了,而當他們做不到時,又會因此感到挫敗。」
抗抑鬱藥的副作用
大多數抗抑鬱藥物的作用機制與酒精或麻醉藥類似:它們通過讓大腦麻木來緩解症狀。維特-多林醫生表示,這種麻木狀態在一些重度焦慮的個案中可能具有治療效果,但依賴藥物卻會削弱(身體)長期的恢復力與韌性。
「此外,有些人服藥後會變得非常無精打采,因此,他們變得有點與生活脫節」,他說,「他們與周圍人的聯繫也會變少。」
服用SSRI(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類藥物也會造成一些其它的後果,其中包括:
• 自殺的念頭和行為;
• 狂躁症(mania);
• 癲癇症(seizures);
• 性功能障礙:包括性慾減退、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女性性高潮延遲或缺失;
• 停藥綜合徵(discontinuation syndrome):突然停藥後出現噁心、出汗、情緒不穩、認知障礙、失眠或其它症狀。
維特-多林醫生指出,有些人即使停藥很久之後,仍然會出現這些症狀。
「大多數青少年在被推薦用抗抑鬱藥時,並不會被告知這類藥物可能會引起永久性性功能障礙。」他說,「有些人——再也恢復不過來了。要是發生在你自己身上,那簡直就是噩夢。」
許多人也沒有被告知,停用SSRI和其它藥物可能會有多困難。在每六到七個停藥的人中,就有一個人受到「長期抗抑鬱藥物戒斷症」(protracted antidepressant withdrawal)的影響。
服藥後情況變得更糟
一項對1148名希望戒掉抗抑鬱藥物的患者(主要為白人女性女性)的調查顯示,其中40%的人出現了持續超過兩年的戒斷症狀,而80%的人表示這些戒斷症狀對自己造成了中度或重度的影響。
這項結果發表在《情感障碍报告期刊》(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Reports)上,指出25%的人無法成功戒藥。
停藥困難可能是因為「長期抗抑鬱藥物戒斷」對大腦造成了損傷。調查顯示,超過75%的受訪者出現了新的症狀,而這些症狀通常不會在患焦慮和抑鬱的患者中出現,包括:
• 頭暈
• 記憶問題
• 注意力集中困難
• 對光線和噪音的敏感度增加
• 頭痛
• 大腦中感到電擊感
• 情感與身體或思維脫節
• 與周遭環境脫節,感覺世界變得扭曲
戒斷症的不良影響還包括:工作能力受損(56%),失業(20%),需要病假(27%),以及關係破裂(25%)。
一項基於69名患者敘述的定性研究描述了兩起與戒斷症狀相關的自殺案例,其中一名患者患有持續了三年的且未能治癒的性功能障礙,在自殺的前一天,她在網上發帖稱,她認為自己無法在這種狀態下繼續生活下去。
根據報導,這位21歲的患者寫道:「說實話,現在我簡直是身處地獄。我已經幾乎看不到希望了。這種狀態已經持續超過三年了,並且情況幾乎沒有好轉。老實說,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
第二天,這名年輕女性自殺了。
另一個風險是遲發性抑鬱症(tardive dysphoria),即長期使用抗抑鬱藥後抑鬱症狀惡化的現象。
「有時候服用這些藥物只會使患者的病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惡化。」維特-多林醫生說道,「醫生們沒意識到是藥物讓他們病情惡化的,然後,醫生們就只是一味地不斷給患者開其它藥物。」
「患者開始同時服用多種不同的藥物,但病情仍未好轉,而實際上是他們最初服用的那種藥物在傷害他們。」
藥物副作用的雪球效應
克里斯托‧韋切爾(Crystal Weichelt)與抗抑鬱藥的長期鬥爭始於她青少年時期,當時她與男友分手後感到焦慮,於是開始服用SSRI類(抗焦慮)藥物。
她告訴《大紀元時報》,當她的焦慮情緒加重後,她的精神科醫生為她開了小劑量的阿普唑侖(Ativan),這是一種用於治療焦慮的苯二氮卓類藥物(benzodiazepines)。苯二氮卓類藥物能夠減緩大腦和神經系統的活動,但容易讓人上癮,過量服用可導致呼吸困難甚至死亡。
她說:「本身就有焦慮的人是非常脆弱的。你會聽從醫生的的任何建議,只為了讓這些症狀消失。那顆藥丸看起來就像是生活的完美解決方案,而且醫生告訴你,這顆藥會幫到你。」
在服用阿普唑侖十二年後,劑量逐漸增長至最初的十倍,韋切爾開始質疑,為什麼自己仍然在與焦慮作鬥爭。
一個臉書(Facebook)上的支持苯二氮卓類藥物的團體鼓勵她慢慢減少藥量。整個過程花了她三年半的時間,即使停藥後,她的病情仍然持續惡化。
她最終臥床四年,足不出戶五年。期間,她的丈夫不得不幫助她進食和洗澡。她的體重只有100磅(約45公斤),由於病情太重,她甚至已經為自己安排了葬禮。但即便如此,她仍然沒有放棄希望。
韋切爾說:「我對上帝有著非常虔誠的信仰,我知道祂會帶我走出風暴,事實也確實如此。我曾對上帝承諾,如果我能活著熬過去,我一定會幫助其他人也走出困境。」
至今,她已經停藥超過兩年了,並成為了一名認證的生活教練,專門幫助其他正在斷掉服用苯二氮卓類藥物的人。
韋切爾在康復過程中使用的一些方法包括:
• 身心可視化訓練
• 誦讀療癒經文與打坐冥想
• 鍛鍊身體(通常從臥床時的小幅度運動開始)
• 通過網上Zoom的社區會議讓人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藥物濫用與誤用
「青少年時期是一個容易受到藥物影響的脆弱時期,而這些藥物可能會被誤用和濫用。」羅格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Rutger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學助理教授格雷塔‧布什內爾(Greta Bushnell)在給《大紀元時報》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這一年齡段的特點是藥物誤用風險較高,冒險行為增多,首次接觸非法藥物的可能性增大,同時也是許多心理健康問題出現的時期。」
布什內爾指出,在幫助陷入困境的青少年時,除了選用最安全的藥物外,還應該考慮採用非藥物治療的方法。
她說,對年輕人要謹慎開具鎮靜劑、催眠劑和抗焦慮藥物(苯二氮卓類藥物等),這是至關重要的。
布什內爾是最近發表在《成癮》(Addiction)期刊上一項研究的第一作者。該研究顯示,自2001年以來,青少年和年輕人因反覆使用鎮靜劑、催眠藥和抗焦慮藥而導致的相關疾病增加了五倍。不過,她指出,這類藥物濫用行為總體上仍相對少見。
布什內爾表示,這些症狀的增加,包括戒斷症狀、中毒和成癮,總體比例仍然較低,這可能是由於檢測率和防護意識提高所導致的。
她說:「用於治療焦慮症狀的藥物在療效和安全性方面存在差異。因此,用什麼方式治療取決於多種因素。例如,苯二氮卓類藥物(benzodiazepines)就存在誤用、濫用和過量使用的風險,因此在某些患者中並不推薦使用。」
根據2023年發表在《成癮》期刊上的研究,苯二氮卓類藥物被認為是治療抑鬱症和焦慮症的二線治療策略,無論是單獨使用苯二氮卓類藥物,還是與SSRI類藥物一起服用。與只是單獨使用SSRI類藥物相比,都會增大用藥過量的可能性。
這類藥物不僅被用於抑鬱症和焦慮症,還用於治療睡眠障礙和癲癇發作等問題。而《成癮》期刊的研究發現,大多數濫用這類藥物的青少年並沒有醫生開具的處方,而是通過朋友或家中的藥櫃獲得的。這種濫用導致的副作用,可能會被錯誤地解讀為焦慮症。
藥物之外的希望
除了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之外,其它一些輔助性做法也可以有效緩解焦慮和抑鬱症。
維特-多林醫生表示,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聚焦在了營養方面。當把超加工和高糖食物從青少年的食譜中去除後,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會有所改善。地中海飲食(是指以地中海沿岸國的傳統飲食習慣為基礎的一種健康飲食模式)和生酮飲食(是一種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適量蛋白質的飲食模式)也被發現與改善大腦功能有關。
許多專門治療青少年焦慮的項目提供了一系列全局性的運動方案和療法,例如紐波特學院(Newport Academy)的項目。該學院致力於治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解決藥物使用紊亂的問題。這些項目強調多種類型的治療方法,包括:體育活動、藝術或音樂療法、社區服務、瑜伽與打坐、充足的睡眠,以及遠離電子產品等。

研究顯示,持續四個月的運動(例如每週三次、每次30分鐘的快速有氧運動)在療效上與使用SSRI類左洛復(Zoloft)藥物效果一樣。
培養健康的手機使用習慣對艾莉婭‧基西克很有幫助。她表示,自己經常暫停使用社交媒體。她的基督信仰和朋友關係也有助於她緩解焦慮,因為這樣能增強她的身分認同和生活目標感。
「生理安全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擁有朋友、擁抱社區,並且有一個超越自我的信仰。」她說道,「我認為,建立面對面的社區聯繫將成為應對這一切的解藥。」
勇敢的蛻變
正如索菲婭所說,從青少年邁向成年的轉變需要一些耐心。正如她的外貌在迅速變化一樣,她的內在性格也在被不斷塑造——索菲婭說這是一個受艱難選擇影響的過程。
索菲婭表示,雖然她重視健康飲食和鍛鍊身體,但有時候她也討厭去做這些事。成長意味著要在沒有動力的時候依然堅持下去。
「除非你去改變,否則什麼都不會改變。有些人要麼一蹶不振了,要麼就是抱著這種心態一飛沖天了。」她說。
索菲婭拒絕使用藥物,而是選擇通過打坐、積極的自我肯定、以及直面恐懼來增強自信心,即使這意味著在社交場合中會滿臉通紅、大汗淋漓。
她成長道路中的重要一環是內在對話——告訴自己,她想要早起,她不想在睡前刷手機,她會鼓起勇氣和人交談。她發現,當她轉變觀念,並將自己視為一個自信和善於交際的人時,這她實際上喜歡和各種各樣的人在一起,即使是一些與她不同的人。
「我不認為,(解決焦慮)問題的答案就是靠吃藥和把自己隔離起來。」索菲婭說,「我認為……做一些對心靈有益的事情,比如去遠足、保證九小時睡眠、吃對身體健康的食物、將自己的身心當作神聖的居所一樣對待——所有這些事情都讓我成長為現在的我。」
如果你(或你所愛的人)有自殺或自殘的念頭,請務必尋求幫助。請記住,你並不孤單。
美國全國預防自殺熱線:撥打或發送短信至988,或發送短信「HELLO」至741741。
英文報導請見英文《大紀元時報》:Digital Despair: How Social Media Fuels Teen Anxiety and Overmed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