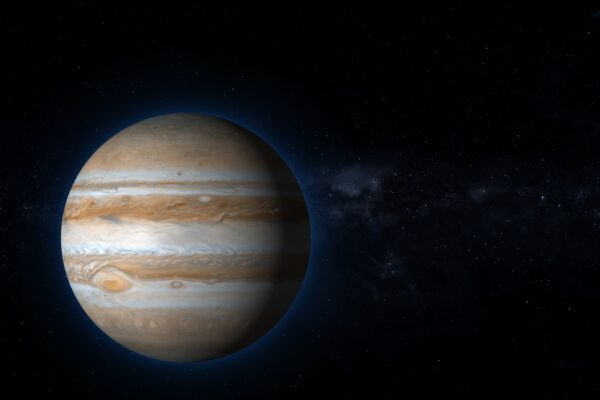【2023年07月08日訊】(大紀元駐舊金山記者薛明珠、專題部記者易凡採訪報導)詩敏是一位護士,她的兒子想要變性,她想通過醫生改變兒子的想法。然而,她原本十分信任的醫療機構,不但沒有幫到她,反而對她兒子想變性的念頭,起了強烈的推動作用。
日前,詩敏向大紀元分享了她的這段歷程。
詩敏和丈夫育有一兒一女,兒子浩賢2001年出生。
詩敏表示,她發現浩賢上幼兒園時,有嚴重的學習障礙。「老師發下來的測驗卷,每頁都打滿紅色叉叉(錯誤符號)。
一頁一頁看下來,家長看著都很心痛,有很大的挫敗感」。
為了讓兒子有個輕鬆的學習環境,2010年,詩敏全家移民海外,來到一個西方發達國家。詩敏不想透露這個國家的名字,文中暫且稱之為A國。
海外的學習環境,雖然寬鬆了,但是浩賢又出現新的狀況。
大約在2014至2015年,進入青春期的浩賢曾向母親表示,想把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切掉。
詩敏當時以為,他不喜歡發育後的身體。家庭醫生也表示,不要緊,持續密切留意就行了。
2017年浩賢讀到11年級,他的一個同學也想變性,他因此深受影響。同年8月,詩敏接到學校護士的電話,「你兒子認為自己是女孩,想要變性」。
這讓家裡一下子亂成一團。
浩賢的爸爸堅決反對,「人怎麼可以這樣?!變性的都沒有好下場」!浩賢因此情緒低落,天天待在家裡,不是躲在被窩裡哭,就是打電子遊戲,或是將自己打扮成女生。
醫生鼓勵變性
為了幫助兒子,詩敏帶著浩賢去看醫生。當時學校護士介紹她,去社區的精神健康中心找治療師,可是事情的演變並不是詩敏預想的。
2017年,詩敏帶著兒子看治療師時,發現治療師並沒有遵循醫療程序。
她表示,一見面就問家長,是否願意參加一個研究項目?然後,拿出一套變性治療方案對家長說,這些青春期阻滯劑、荷爾蒙等等藥物都是安全的、都是可逆的,還說可以給孩子,提供頂級的變性外科手術。
詩敏說,這個治療師給她的感覺更像是一名推銷員。
治療師還對浩賢說:「雖然你已經16歲了,過了發育期,但我仍然可以給你提供青春期阻滯劑。如果你父母不給你藥物,他們就是你的敵人。所有人都應該尊重你的選擇。」治療師還問浩賢喜歡的(女性)名字是什麼?喜歡的(性別)代詞是什麼?
詩敏後來發現,這個治療師私下用女性的名字和代詞稱呼浩賢,並瞞著詩敏,肯定了浩賢的女性身分。
浩賢從此開始對父母產生抗拒心理,除了見這個治療師之外,都不出門了,以致徹底輟學。
詩敏還發現,以前浩賢上男廁所是沒問題的,他的身分證上寫男性也不成問題,可是自從去了醫療機構之後,這些就都變成問題了。
她說:「你知道嗎?他們要求浩賢填寫一份問卷,上面的問題是,你是否因去男廁覺得焦慮,覺得有壓力?看到身分證上的性別,你會感到壓力嗎?」
「我真想罵人,這些醫療機構在製造問題。實際上他(浩賢)沒有壓力,是醫療機構的醫生告訴他,他應該有壓力。所以從那以後,我兒子再也不去男廁了,也不搭乘飛機了,因為身分證上的性別是男性(搭乘飛機需要用到身分證)。他哪兒都去不了了。」
「我一直信任整個醫療機構,相信醫療機構是幫助家庭的。但是我發現,我兒子接觸治療師越多,與父母的對抗就越大。我發現,我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聽信學校護士的介紹,去見那個治療師。我是帶他去飲醫療機構的毒藥!」
詩敏帶著兒子見這個治療師約有六七次。
「我和兒子的關係本來很好,他們這樣做,使得兒子把我當成了仇人。」
醫療機構不信任父母
詩敏表示,浩賢自從看過治療師後,不僅對抗父母的行為越來越嚴重,甚至拿刀自殘,搞得家無寧日。
一天24小時都要有人看著他。到了晚上,詩敏與丈夫還要輪流打地鋪,橫睡在家門口,防止浩賢半夜跑出去自殺。
有一次,浩賢又要自殘自殺,父母送他去醫院急救。
急診室的護士對浩賢說:「你來到醫院就很安全了,沒有人可以逼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我們會認同你的身分的。你在家不安全,你可以到醫院來。」
浩賢在兒童醫院精神科,住了七天後出院。在此期間,詩敏尋求另一位大學教授的幫助。
浩賢出院時,主治醫生嚴厲警告詩敏說:「如果你諮詢那位教授,接受那位教授的治療方案,我有權收治你的兒子兩天。」
詩敏感到異常氣憤,「尋求不同的治療方案,難道不是病人的權利嗎?!主治醫生說我們不同意孩子變性,說父母在逼孩子自殺,並以此為藉口,想從父母身邊奪走孩子。」
「我兒子就是跟他們學會了這一招。他要脅我們說,『如果你不給我青春阻滯劑,我就會死,我就自殺。』」
在浩賢住院期間,一個精神科顧問和一個資深社工要求浩賢的父母,必須每天到醫院與他們面談一小時。
「實際上,他們在調查我是否有虐待兒童。」詩敏說。
詩敏還表示,在出院那天的出院會議上,如果沒有追問兒子的病情,主治醫師連診斷結果,都不會告訴家長。
他們還填好了一份保護兒童免遭虐待的「兒童保護表格」,並告訴詩敏,該表格已填妥和提交。
詩敏很生氣地對他們說:「我移民到A國,就是因為我的兒子有學習困難,我希望他有一個輕鬆快樂的學習生活環境,我虐待兒子有什麼意義呢?」
這次的經歷讓詩敏意識到,這裡的醫生,根本就不打算給她兒子做任何治療,還有可能從她身邊奪走兒子。
「他們不但不提供幫助,還把父母妖魔化。他們不是在治療我兒子,而是在治療我,逼我接受兒子的變態行為。」
她說,「我覺得很傷心、很心痛。我也是醫療人員,為什麼醫療人員不是幫助人們恢復健康,而是傷害人們呢?父母不但被壓迫,還被妖魔化。」
詩敏受到很大的打擊,感覺受到很大的傷害:「兒子為什麼這麼不開心?就是醫療機構這些人,把所有原因都推到父母身上,指責父母不認同他的性別選擇,不贊成他變性,讓孩子與父母形成敵對。」
毅然選擇離開
有過這次經歷之後,詩敏再也不敢帶兒子,去主流醫療機構看醫生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2017年年底,詩敏決定離開A國,搬到亞洲某國。
儘管浩賢同意搬離A國,但是旅行對他來說,是一種巨大的痛苦,因為他無法接受自己的護照上寫著「男性」。
浩賢躲在機場的殘疾人廁所裡,哭了兩小時,最後總算抵達亞洲某國。
安頓好新家後,詩敏為了幫助兒子煞費苦心,想出了一種獨特的方式。
她勸浩賢學一門手藝,因為學了手藝可以掙錢,浩賢爽快地答應了。
詩敏還私下和一位玩具公司的老闆朋友商量好,讓浩賢每天到其公司上班,由詩敏負責支付浩賢的薪金。
為了防止浩賢賺到錢後亂花,詩敏還讓公司老闆,以消費卡的形式支付工資。
詩敏說,浩賢在玩具公司開心地工作了一年。
「上班有同事和他一起工作,下班後,他們就一起去玩,大家一起吃飯,一起吃宵夜。公司還讓他和其他幾個男孩子一起外出,參加玩具比賽,他們還一起穿著公司的制服照相。」
在這一年裡,浩賢還曾發短訊給A國的舊同學說,「你可以叫我浩賢了,叫我的男孩名字」。
同學問他為什麼,他說他在玩具公司上班很開心。不過浩賢並不知道,詩敏為此花了很多錢。
但浩賢的狀態並不穩定,又花掉了家中的大量積蓄,所以這份工作僅做了一年。
他的父親也不支持這麼做。不過在這一年中,詩敏畢竟看到了希望。
接下來的幾年中,浩賢沒有再工作,整天沉迷於遊戲,發脾氣時,還有暴力傾向,會摔砸各種物品以及打人,詩敏的頭曾被他打破,身上有多處瘀傷。
但是夫妻二人,也逐漸摸索出一套應對的方法,當兒子發脾氣時,他們就離開,讓他自己留在家裡。
經過幾年的相處,儘管詩敏和丈夫仍然反對兒子變性,但是應對方式沒有那麼激烈了。
詩敏表示,丈夫發現兒子偷買女人的內衣,會平靜地告訴兒子,把這些東西扔掉。「這要在以前,父子倆早就大戰一場了」。
詩敏說,過去的一年,浩賢變得平靜了,丈夫也變得越來越溫和,父子倆的關係越來越好。
丈夫下班回家總是問兒子,晚餐想吃些什麼。上個月開始,丈夫的工作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忙了,他表示要多花時間陪他的兒子。
詩敏表示,他們學會了以一種非常平靜、冷靜的方式與兒子相處。他們不期望兒子能發生多大的轉變,只要他活著就好了。
假使孩子真的做出極端行為,他們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5月份,詩敏的丈夫帶著浩賢,成功完成了一趟海外郵輪之旅。
當浩賢從海外旅遊回來後,有一次敲開父親的房門問:「我們可以一起去國外旅遊嗎?」這在過去六年裡,都是無法想像的,詩敏開心地笑了。
詩敏表示,她希望兒子25歲之後,大腦發育得更完善時會變得更理性,也希望兒子能夠到處旅行,增長見識。
詩敏認為,只要家庭關係、他們父子的關係越來越好,就會打破更多的隔閡,兒子會感到更多的愛,可能就會找到生命的出路。
詩敏的教訓
在受訪的過程中,詩敏多次檢討自己,她表示,自己在整個過程中,得到了很多教訓:
一、浩賢是一個需要特殊照顧的孩子,父母應該花更多時間在他身上,但他們最初花的時間不夠。特別是浩賢在學習跟不上的時候,應該告訴他,「讀書並不重要,開心就可以了」。當浩賢與別的同學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他就想逃避,甚至誤以為,換一個性別身分可能會得到別人的尊重,其實不然。
二、浩賢喜歡結交朋友、社交,但他不知道如何與人相處。家裡給他連上了互聯網「真是大禍害」,如果家裡沒有互聯網,不能玩遊戲,他會願意出門,與更多的人相處,也就不會這麼孤僻了。
三、在浩賢想要變性的過程中,西方的醫療機構起到了有害的推動作用,它們過於強調個體的所謂自由。同時在變性的產業鏈中,部分治療師很可能有利益關係。所以,當初盲目地相信一個自己並不了解的治療師,是她最大的錯誤。
為了保護孩子的安全、健康和隱私,文中的名字都是化名。◇